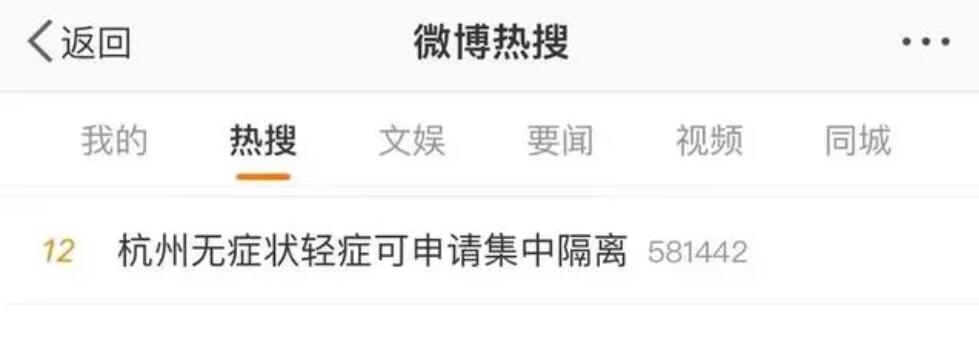一座城市有CBD
一座村镇也有CBD
如果说CBD是城市商业发展的中枢
那么“村BD”就是乡村振兴的晴雨表
不久前,记者来到巢湖市槐林镇
记录下一个村镇最繁华步行街的春节消费大战

奶茶大战的一触即发
在巢湖南岸沿巢庐路自西向东,就会穿槐林镇而过。
巢庐路与槐青路的交叉口是整个槐林镇的黄金路口。站在这个路口,向南是槐林镇镇政府;向东则是槐林车站;向北望去,则是全镇的商业最繁盛的“步行街”——槐林路。
“整条街大概有200多家市场主体。”槐林市场监管所的方胜利告诉记者。槐林镇下辖两大社区、14个行政村,165平方公里内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当属这里。
作为一镇,槐林镇购买力很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槐林镇就“以渔网兴镇”,第一波人先富起来。巢庐路两侧,渔网渔具相关的门市部比比皆是。槐林镇也成为全国最大的渔网生产基地,镇里有很多工厂,三班倒,24小时都有人上班。
产业带来财富,财富带动消费。“镇里消费可贵了。我们有时候都不在镇里吃饭,开车去(巢湖)市里吃(会更便宜)。”一位槐林镇居民说。
而槐林镇更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巢湖市有人民路,而槐林路就是小“人民路”。
槐林路北面本来有一条“老街”,是镇子的旧商业中心。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腰包渐鼓,新的品牌和业态层出不穷,狭窄的老街显然容纳不下一座镇子的野心。槐林路接棒成为当之无愧的全镇“CBD”。
在这个CBD里,有沙县小吃、五金日杂百货、口腔诊所,有婚纱摄影、海澜之家、奶粉专卖;有8号站台、韩流服饰、永辉美发;有塑形店、新华书店和假日金冠蛋糕房。小镇三十年沉淀的代际消费在这里混杂而生,一派和谐。春节期间,“CBD”从早上堵车堵到晚上,路两边划的停车位根本不够用。

这里也是小镇消费升级的风向标。在槐林路上开“奶茶先生”的吴彩霞自己是奶茶爱好者。“奶茶先生”距离槐林中学仅有400米,她对消费的变化深有感触:“现在一个中学生口袋都装100块钱。”
吴彩霞初中在槐林镇下辖的海如村上学,第一次喝奶茶是粉冲的奶茶,里面有珍珠、椰果,一块钱一杯。
十几年之后,沪上阿姨、悸动烧仙草等连锁品牌都已入驻槐林镇。以槐林中学为中心,整个槐林镇已经拥有十几家奶茶店。奶茶大战一触即发。吴彩霞的奶茶店每天都营业到晚上十点。“春节生意不错,但压力也很大。前一天晚上9点多,还有好几拨客人。”
温州商人主导的商超
当年,万达广场鼎盛之时,曾有“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说法。同样,槐林路的兴起与一座商超的崛起关系密切。
属于槐林路的“万达”是一家温州人开的大型超市“永乐辉”,位于槐林路北端,夹在巢湖市巢南家电城和童贝母婴城中间。超市的门脸不大,进门的地方安排了“正新鸡排”招揽顾客,鸡排店老板周东红在这里做了三年生意,炸串的香味是小镇居民逛“永乐辉”的记忆之一。
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温州人的商业触感。
“永乐辉”是一家连锁商超,大本营在南京。槐林镇的这家在2016年元旦开业,面积2000平方米。除超市之外,还包括面包房、安踏等四五家主力店铺。置身其中,你不会觉得和巢湖和合肥的商超有太大区别。
“永乐辉”刚开始名字叫做“大润发时代”。以上两个名字都有山寨之嫌,但却是小镇开店最佳品牌战略。
在“永乐辉”进驻之前,槐林路两边店铺稀稀拉拉,并不成气候。但永乐辉入驻两年后,人流带来商机,新街彻底超越老街,一举成就“小镇CBD”。
“永乐辉来了之后,周边店铺的租金涨了两三倍。”超市斜对面的一位开店者说。

超市的管理者翁浩富是个斯文的商人。他整个春节没回温州,一直在槐林盯着生意。永乐辉整个春节都不打烊,晚上九点关门。“春节生意比去年好太多。”他指指外面:“每天晚上(槐林)路上都堵得厉害。”
实际上,“永乐辉”在镇上也面临激烈竞争。主要的挑战者是老牌商超“好又多”(2014年开)和新晋入局者“大乐购”(2022年开)。尤其是后者,就开在槐林镇菜市场旁边,令翁浩富倍感压力。
2020年,他曾经主导过一次商超重新装修,投入近百万元,拓宽了通道,调整了货架和布局。这次调整令永乐辉重新成为小镇日用品消费的首选地。
“‘大乐购’刚开始很猛,但最近势头下来了。”翁浩富分析:“它那个位置是很好,但是在二楼,年纪大的人都不愿上去。”
蓝莓商人的合肥红利
“永乐辉”的“一哥”地位也是其货品档次奠定的。
沐俊珊是“永乐辉”的水果供货商。他的果园位于槐林镇潘付行政村老沐村,距离槐林路不到2公里。“蓝莓算是高档水果,我们给上海和合肥的商超定期供货。”
在槐林镇,“永乐辉”定期从他手里进蓝莓。蓝莓成熟的时候,卖场就会给沐俊珊打电话要货,一天能卖4箱左右。
沐俊珊2015年从上海回到老沐村,承包了200亩果园,一开始就主攻“蓝莓”。
“因为上海人喜欢。”沐俊珊说。但他没想到身边的消费提速这么快。在他的蓝莓种植成功后,曾邀请一批“先锋顾客”来果园试吃蓝莓。“当时客户的接受度非常差,也没有(吃蓝莓的)经验。”
但没过几年,情况就大变。去年疫情,他没有再往上海卖一箱蓝莓,在合肥周边地区就把货全部卖光。他试着在微信朋友圈中“招募”了下会员,一把就募到200多人。
他的生意已经和合肥发展绑在一处。他有一套“驾驶兴奋理论”:“从合肥市区到槐林镇,走环巢湖大道2个小时可到达,此时驾驶员还处于“兴奋状态”。“这时候的消费就是成立的,就可以来农场,搞个采购、垂钓、农家乐。”
沐俊珊喜欢老沐村,也喜欢槐林镇。2015年他在上海已经拥有5家水果超市,决心回来开果园,但他的“返乡创业”几乎没有人支持。
至今,这个决定也毁誉参半。这也是最令他焦心的:村里的年轻人出去就不会回来,人越来越少。他有一个朋友在镇上开公司,月薪六千的人降薪四千也要去合肥。
一座“村BD”的成型有两个底层逻辑:第一是钱;第二是人。财富的聚集引导消费的聚集;人流的聚集带来人气和创新;而人是整个商业的基础所在。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能否持续繁盛,槐林路亦在面对变局。
吴彩霞的奶茶店正在应对消费年轻化的变局。
翁浩富在思考“跑腿外卖平台”对小镇商超的冲击。曾有平台找他合作,但高额的中间费用几乎抵充了商品的所有利润。为此他很困惑:“如果我一旦涨价,镇上的人看到价格这么贵,是不是就不会来(实体店)了?”
沐俊珊则希望招募更加年轻、更具创新品质和商业精神的新鲜血液加入他的果园。
“过完年我就快50岁了,但是在村里我还算是一个年轻人。”在他的身边,是空荡荡的果园和一条名为“小花”的流浪狗,名字是他的女儿起的。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梁巍 常诚 文/摄 周继龙/图 政经八百工作室出品)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