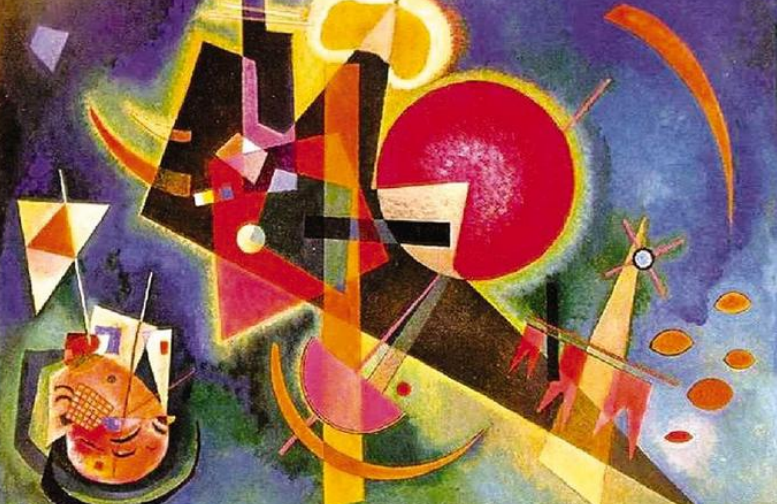内心常有甘泉
◎徐燕
《烟霞里》 魏微/著
魏微的语言一直很好。这部小说让人看了不烦,亲切。一个女人的编年体传记,由女作家写来分外有感,而且由于主人公正是70后,和我同时代,看这里面的故事,如同是一个通往过去的镜像,一年年对照下来,仿佛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回溯。据说作者本打算把主角写到五十岁,但限于篇幅,草草结束于四十一岁。这足够了,时代与命运的组合交响,已描绘出一个女青年在时代的光影下,如何划出自己的痕迹。
《黑镜分身术》 陈崇正/著
陈崇正的小说之前我没看过,看了这一本,觉得想了解他的作品,一本就够了。这是几个中篇的集合,但中间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牵扯的,形成了奇妙的前后效果。尤其始终在其间的那个村子:半步村。如同香椿树街之于苏童,沙街之于林白。这个半步村之于陈崇正,应该是有同样意义的,标识性是如此的明显,意义不下于马贡多镇之于马尔克斯。那些来历不明又神秘莫测的人,比如破爷,即使他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比如污染当地的水源和引进色情,也让人恨不起来,反而对于他后来的结局起了一些嘘叹之心。这都是传统中国的根子在里面,子嗣是重要的,家业是重要的,可是,归根结底,这片山水所系也是重要的。

《亲爱的蜂蜜》 笛安/著
去微博围观了笛安,她确实是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觉得这不折不扣是一本十级恋娃小说,生在她家的孩子一定生活甜如蜜。一个离过两次婚的男人和一个有孩子离了婚的女青年的故事,主角是三岁的孩子,从题材来说已可归为都市传奇。小说也掺进了朋友老杨一家的故事,以及天降疫情这么诡异的时事。这世上总有我们感叹甚至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发生。我感觉到了文中的能量,应该也能算是一种激情写作吧,处处都在流露幸福甜蜜。其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取得好:熊漠北,崔莲一。在看了好多小说根本不记得主人公名字的当下,这个发现也挺令人高兴的。
《入魂枪》 石一枫/著
石一枫所有的小说都爱看,我喜欢他说故事的手法,不论结构还是语言,即使这次是我不太懂的电竞。
这个故事有点阿城《棋王》的影子,不疯魔不成活,里面两个瓦西里,应该是自闭症患者吧,但是,电竞游戏给了他们熠熠生辉的可能,还有天不绝我的慈悲。
印象深的人物除了主角,还有姥姥和姐姐,都描写得很生动,语言戏谑,确实很有生活。语言出彩,是石一枫最强项,讲好一个故事,他做到了,仅此一点,秒杀目前大多作家。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著
没想到这本书还真的挺好看,当时看的时候就感叹叙事的方式很现代,它活生生就是一部剧本呀,场景化特别明显,后来听说荣获了今年的茅盾文学奖,也就不足为奇。题材也是当下比较主流的谍战片,而内容为半虚构的当年国共合作失败后,上海的中央机关要撤到根据地的路线的事件改编,形势危急而敌我难分,故事弦一直绷得紧紧的,还是很精彩的。
我喜欢的书
◎许冬林
《芸斋小说》 孙犁/著
孙犁晚年创作的笔记体小说《云斋小说》沉郁深邃,尤为感人。晚年孙犁的文字已由早期的“土膏微润”一般的肌理丰润转为“疏影横斜”一般的萧冷和清淡。《忆梅读<易>》一篇中,孙犁回忆自己一九五八年养病期间在无锡去梅园访梅遇雨的情景:“有一次,遇到下雨,我一个人在园中,流连了整整一个上午,并在梅园后院一大间放农具的房子里,惆怅地望着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追索往事”。纵览《芸斋小说》,其中所流露的情感、所记述的内容,大抵也可以概括出晚年孙犁的心境和文章,是:落泪梅花,追索往事。
《活着》 余华/著
余华善于化重为轻。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善于使用节奏感来处理情节、场景细节和语言,呈现出鲜明的节奏美学特征。《活着》主人公福贵一生经历8次不幸,他不断失去亲人——父母、妻子、儿女、女婿、外孙,最后剩下他自己一人,和一条老牛相伴。这样漫长的苦难,余华将它们裁剪成若干片段,他让主人公福贵像个游泳者一样潜入往事里,娓娓道来地讲述一段,再浮上水面,回到现实的田头树下,同时附上一段“我”的所见所感。如此,福贵漫长的苦难一生被作者设置在一个下午的田头树下,像乐章一样,由福贵来表演。如此,福贵一生的故事,被裁剪成了乐章式的“民间歌谣”。
《生死场》 萧红/著
鲁迅在序言里说《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理和新鲜。”这部小说的独特性还包括诗性的语言、散文化的叙述风格。特别是在时空的表现上,呈现出时间上轮回、圆形的形式之美,空间上延展所带来的广阔内容与深重主题,以及语词的色彩渐渐抽离所形成的雄迈凝重,从中折射民族精神。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著
小说通过聚焦情欲来透视女性本体生命意识和文化内涵,彰显女性话语下的情欲书写的生命力感、诗意美感和情欲的永恒、光明和纯洁。王安忆曾说:“《岗上的世纪》,它显示了性力量的巨大,可以将精神扑灭,光剩下性也能维持男女之爱。”小说中的女知青李小琴为争取回城的招工推荐表,作为主动的性的诱惑者试图通过性爱来交易,达成世俗的功利目的——回城。男女主人公也逐步在这不断推进的情欲中成长,获得对自身生命意识的深深体悟。界定《岗上的世纪》的写作内容时,用情欲书写来概括比用性书写来概括要更为妥帖。
《德富芦花散文》 德富芦花/著
德富芦花面对自然、日月星辰、村舍山野,都怀有一种赤子般的初心。读他的写景散文,形象、细腻,草木山川如在眼前。他的写作,是心贴在泥土上写的。读他的文字,能感受到他的心灵温度,也能捕捉到一个岛国真切而丰富的颜色、气味和声音。作家写景,用语简洁,极富层次。在散文《利根秋晓》里,从黎明的霜花犹存,夜色微暗,写到鸡声隐隐相呼,然后天色微明,水雾升起,再到旭日东升,光芒照耀河面。大自然像花朵一层一层打开花瓣,无声而充满生机。
书中有光
◎钱红丽

《别雅山谷的父子》迟子建/著
当代女作家中,一直喜欢迟子建的文笔。宛如一个不老神话,她每一阶段的小说都经得起审美。不可多得的是,始终弥漫于小说中的诗性表达,尤为令人着迷。这本小说是几个中篇结集,第一篇《亲亲土豆》,是二十多年前读过的,如今重读,依旧好。她写平凡夫妻之间的感情,一向温暖朴素动人,以很小的视角去展现暖老温贫的日子,有苦有悲,也有乐。正是那一点乐,构成了漫长生命里的甜头,回味无尽。还有《一匹马,两个人》,同样写小人物,关于一对老年夫妇相依为命的生活。许多年过去,那种温暖的情绪始终荡漾着的,是幽暗前行路上的一点微光。
比如《采浆果的人》《布基兰小镇的腊八夜》,河流一样倒映出作家唯美的眼光和笔调,审视着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命运,艺术地展现生活的细琐平凡,无一例外都带有浓厚的大自然灵性。每次翻开迟子建的小说,总有一种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甘心沉浸。她小说中平凡人身上闪耀着的一种冒着热气的原始生命力,传达出了一种珍贵的本真与澄澈,好得令人叹气。
《小窗幽记》 陈继儒/著
这本书,我是在做饭间隙一点点读完的。于一锅蒸菜定时的二十分钟内,就可以读上几页,先看原文,再对照着白话译文,有些翻译不太准确,找支笔圈一下,回头空闲时,自己再译一遍。比如:高卧闲窗,绿阴清昼,天地何其寥廓也!译文为:在小窗下高卧,绿阴洒落,天地是多么阔大呀!将:“寥廓”译为“阔大”,明显不妥。读书的快乐便在这里,不要浮光掠影,要深思深究,一个词一个词地去抠它背后的涵义,慢慢地让自己变得通透,一如秋天的晴空那么辽阔无际。
以《幽梦影》《幽梦续影》《小窗幽记》为代表的明清小品,均以一个“幽”字贯穿,清幽虚静,是锻造散文笔法的楷模,与王维后期的诗歌同为一脉,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也是一个人的生命趋近自由之境的表达。

《故事新编》 鲁迅/著
每临秋日,除了看看秋水夕阳,还格外喜欢读读鲁迅。鲁迅的存在,原本就是秋风秋雨中一眼望不见尽头的萧萧芦荻,风吹一头白雪,萧瑟又庄严。一部薄薄的《故事新编》常读常新,尤其《铸剑》,简直可以拍一部电影,两只被砍下的头颅在鼎沸的汤水中战斗,何等魔幻主义。鲁迅在简约、精炼的叙事中,所追求的纵深感,以及他天然的文字禀赋,无人可以轻易超越。造人造到神烦的女娲,一年到头吃乌鸦肉炸酱面的后羿一家……一个个经典形象,均在鲁迅高超的叙事中复活并颠覆着。《出关》中的老子,《起死》中的庄子,《非攻》中的墨子……每一年龄段去读他们,自会产生新的奥义。这也是经典的意义所在。
《我与地坛》史铁生/著
史铁生是当代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作家以残缺的身体,写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精神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着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地坛只是一个载体,这里有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
囿于不能行走的身体,他一直困于逼窄的空间之中,可是,通过年常日久的坚韧,作家硬是将一个井口大的生存空间开拓得无限广大纵深——好的文字是可以直通宇宙浩渺的。这也是一部人类精神的涅槃之书,永远给予人正向的力量。
《苏东坡传》 李一冰/著
作为一名生活的失败者,每每遭遇曲折之时,总是条件反射意图搭救自己一把,比如时不时翻出苏东坡传记读读,从而借点力,处变不惊走下去。
几十年来,不知读过多少遍苏氏传记。起先是林语堂版本,这次换了李一冰版本,发现一处细节。
苏轼海南时期诗作中,有一首《次韵子由浴罢》中,其中一句“老鸡卧粪土,振羽双瞑目”,令我大为震动。62岁渡海的苏东坡,比黄州时期还要绝望——“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几乎要给自己备棺的程度了。可是,慢慢的,这个人的内心又如何起了转折?连理发、泡脚、午睡都入了诗文,写得兴致勃勃的,是真的赤子心,并非强颜欢笑那种。
这一句“老鸡卧粪土,振羽双瞑目”的意象,直叫人拍案惊坐起。不曾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大约隔膜得很。乡下鸡鸭白天在外疯,到了晚上一律被赶往狭窄漆黑的鸡舍,遍地皆粪。
自比老鸡倦马的他,一样见天地,守住了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尊严与体面。

《我以文字为业》 厄休拉·勒古恩/著
一生获奖无数的勒古恩以小说名世,我却格外喜欢读她的散文随笔——我热爱阅读一切小说家的散文随笔。小说是他们的台前表演,我喜欢去幕后看看卸了妆的真人,遵循文字的脉络与其交谈,从而一窥思想。
这是一本随笔、演讲、杂谈三者交织的书。第一部分,自文学创作、书籍阅读、科幻与现实、动物与文化,到语言与写作、家居生活等,她无所不谈,又无不有趣。尤其对于女性处境以及女性文学创作的阐述,一针见血,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写者洞穿一扇小小窗口,原来,同一平行时空中,一直有着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同行者,我们并非孤独无援。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
赫塔·米勒/著
作家“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这本书相当于一部自传。赫塔讲述了自己自罗马尼亚小村庄到诺奖领奖台的传奇经历,相当于一片了解作家生活与创作的背景板。她通过敏锐的视角与克制的语言,出入于现实生活与虚拟的文学之中,熔淬成一篇篇锋芒毕露的文章,刺破罗马尼亚社会的表象。
“通过爱,人可以更珍惜自己一点,在监督国度的被忽视与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正因如此,爱成为自由缺乏症的替代疗法。我没见过哪个国家的人们对爱如此饥渴。我工作过的所有工厂、学校,各个阶层,到处是婚外关系,男人女人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工作岗位的艰辛使他们对任何环境都能处之秦然,在工厂的某个隐秘肮脏的角落体验被爱的快乐,能让流水线上或写字台边的痛苦变得可以忍受。”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