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中绕山
◎张妍
如果不是有座蜀山,我来合肥定居的时间还得往后再推十年。
北平原的黄土地一踢一脚土,站在村东头能一眼望到村西头,刚犁过的田地平展延伸到天尽头。年少的我曾以为,天那头也是黄土地,天高地矮人永远摸不到云。
小学二年级背会一句古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当时有些犯迷糊,找到有学问的大人问:“人搁云里咋采药呢,他师傅可是神仙?”他们说,山里有白云,能把人围在云里面,不止有云,还有溪水、泉眼,还有昂贵的灵芝与石斛。
那时,平原孩童眼里最高的山是“曹四孤堆”,四座用黄土堆起来的高坡。我时常跑到最高的“山顶”放风筝,边玩边等着有一天白云把我围起来。
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后会疯狂弥补什么。从小缺“山”的我,谈不上疯狂,却也处处刻意,不但把住处选在离蜀山很近的地方,而且每隔十天半月都得去大蜀山绕一圈。赶6:17第一班地铁去大蜀山,七点之前人少安静,绕山锻炼的居多;七点之后老人孩童不断,游山闲聊的居多。
进入山门,人不自觉安静下来,两千米上坡路又高又长,说话、嬉笑、悲伤、哭泣,耗气耗神的行为,会让你在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乏累如老牛。扔下尘杂内耗,静静走过这段上坡,犹如重新拧紧了灵魂与肉体,时常在庸常中分离的两者,在一呼一吸中再次合二为一,共同面对大山的考验。心神不定、意志不坚、体力不支的人,常在这段上坡路中放弃前行,在坡顶转弯处或犹豫或决绝地转身回去。余下的绕山路,没有太长太高的坡,约莫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山顶。
处暑过后,凉意徐徐,树荫斑驳,楮树挂果,楮桃红得鲜艳,抬手可摘的距离,总让人想起小时候舔舐楮桃的丝甜。山道上林荫罩顶,行走处绿意满盈,黑脉蛱蝶随着脚步翩飞如花,鸟叫虫鸣是蜀山赐予的疗愈BGM,行走其中,犹如被滋养七情五志,润泽五官五华,身体细胞在负氧离子的氤氲中焕然一新。
又去看那棵百年麻栗树,每次绕山摸摸它,才觉圆满。树下竟然有一束细心包裹的野花,结籽的野草穗中间有一支粉紫色的山花,看上去天然纯洁。前天是七夕,许是某个中二少年表白心迹的花束,包花纸上写着“幸运之花”,祝愿他(她)在感情上一直幸运。
站在山顶南平台俯视整个城市,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笔直绵长看不到头,清晨阳光照耀下,这条路闪闪发光,好似城市的银河。以前没在意过,现在想知道它具体的路名,查了半天地图,也没找到准确答案。
下山时,一位胖乎乎的大哥走在我前面,他走得极慢,像是在等谁。即将超越他时,一只黄背白腹的小猫从我面前跃过,小猫脸是白色的,沿着嘴周醒目地长了一圈黄毛,可爱又搞笑。它蹿到胖哥脚边,也不喵喵叫唤,只是在他脚下使劲磨蹭打转。胖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包,将里面的东西倒在路边水泥台上,远远看过去,一粒一粒似是猫粮。
胖哥转身快步下山,小猫跳上水泥台开始饕餮,一人一猫,投食吃食不过30秒,期间没有任何言语交流,却十分默契流畅。想必他俩都是内向性格,不善表达,心意相通。
城市里的山温良大气,不管是当地人外地人、内向外向,都能一并包容。它也是我中年的靠山,在我背着35岁的沉重走向它时,它像一位长者及时托起了沉重,弥补了缺失,又给了我进山疗愈的权利,不必央求任何人。
孤独漫步者
◎冬晴
湖是巢湖。住在湖边,像睡在清凉的梦里。每日晚饭后,去湖边走走,成为像呼吸一样自然又必须的事。
特别是黄昏,沿着包河大道或者庐州大道,一直向南,向南,抵达合肥之南,抵达城市的边缘。那白茫茫的一个大湖碧波荡漾,在视线末端一点点贴近。然后,闻到柳树和芦苇的清香,闻到水的潮润之气,感觉从城市中心奔逃出来的那个滚烫尖叫的自己在湖边的微风里慢慢降温,慢慢寂静,慢慢和水天一色相融在暮霭里,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晶莹清透的那一部分。
去湖边走走。是的,去湖边走走。每一个夜晚来临之时,总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响起,是我跟我自己说。
借着融创茂那边的灯火闪耀,我走在湖畔草坪之间的水泥路上,是沿湖而走,一个人,向东,脚下的路渐渐暗下来。如果向东一直走下去,走到黎明,就可以踩到草坪上的朝阳初升。晚风吹动湖边湿地上的芦苇,发出簌簌之声,那是叶子在跟叶子对话,那是叶子们在跟湖水对话,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里,总像是暗暗流淌着各自懂得的深情。如此,草木不孤独。孤独的是人。
在夜色尚明之时,我喜欢沿湖快走,胳膊甩出风来,身上、额头上覆一层细汗,然后又被夜风一层层吹干。这种大量出汗又被风尽数吹干的感觉特别爽朗利索,有种在北地走路的感觉。我从前不喜欢北方,在北京读书时总认为那里空气太干,皮肤再怎样补水,一眨眼又干得像茶叶。后来消除了容貌焦虑后,反倒喜欢起北方来,喜欢它的走路身上不存汗,是汗水一出就被干燥的空气蒸发了。所以,课余时间到鲁院附近的红领巾公园漫步,便成为一段美妙的记忆。
我在巢湖边的散步几乎都是黄昏和晚上,有时向东走,能一路经过不远处的安徽省美术馆、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安徽创新馆。脚步两边,一边是夜色巢湖的自然风光,一边是几家展馆外霓虹闪烁的人文景观,走在这样的风景里,真像是走在梦幻般的琉璃世界里。我快步在夜风里穿行,在远远映照过来的迷离灯光里穿行,感觉自己的步伐也变得轻捷起来,很有一种少年感。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像是在这种行走里啜取了青春般的能量,以供应我在白日里再向城市的腹地,向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奔赴。
心情低落的时候,也去巢湖边走走。夜色是黑的,柳树和芦苇是黑的,草坪是黑的,我的影子也是黑的。我的黑色的影子在慢慢的行走中像是被朦胧的星月光芒给滤去魂魄,我踽踽独行,像是一路在草坪上,在树影里,寻找我的魂魄。
我常常把湖水那样浩瀚的忧伤在夜晚的湖边边走边泼洒。我白日在城市的腹地隐藏自己,我隐藏我的眼泪,隐藏我的叹息,我骨骼高耸,像一只威武的兽,所向披靡。夜晚是我的,夜晚的湖是我的,夜晚的脚步是我的,我为自己慢走,在风里,我为自己剥去带血的羽毛。我在湖风徐徐吹拂中,告诉自己,就像此刻在湖边的独行一样,人世间的白日里,有许多路,我要握紧自己的影子,咬牙含泪走下去。走一走,走远了,我的脚步就成了风景。
许多年前,遇见一幅古画,好像叫“孤往”,一个古人,抱着一把琴,往树林深处去。我不知道,在树林深处,是否有一个等着听他琴声的人。
也许没有吧。灵魂深处,我们都是孤往者,寻寻觅觅的孤独漫步者。
好在还有这静夜,还有这浩茫的一片水,陪着我在城市边缘漫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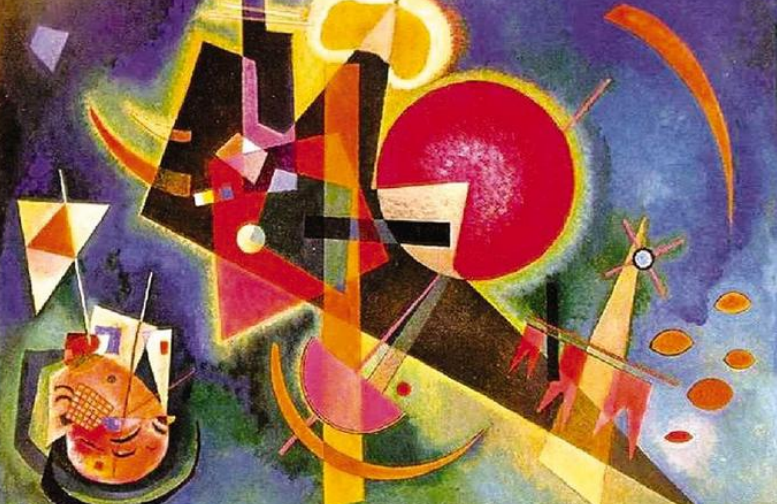
一年走了86个马拉松
◎小麦
别人眼中我是一个疾步分子,其实,最开始走路的原因很简单,我不想自己变成一个胖子。
当意识到岁月缓缓辗压而来,将这具肉体崩坏,不止是容颜的速朽,更是身体各个零件都在慢慢失灵,不听使唤,老之将至的恐慌接蹱而来。开始认真运动,其实是一场针对中年危机的正面抵抗。
大约是2013年左右开始走路的,那时的我接近四十岁,日当正午,饭局极多,生活和体重一起失控,渐渐就面目可憎,每周两次的羽毛球好像毫无帮助,眼见得一个双下巴大脸盘肥腰身的女胖子呼之欲出。不忍照镜子的当儿,契机来了,拜访的一个老客户,惊讶发现短时间不见,他已从油腻变得清俊,不过是走路半年的收获。
在他的引荐之下,我加入合肥欢乐暴走团,算是正式迈开了脚步。
比起大多数运动,走路的好处自不必说。最重要在于它可以:随时随地。
羽毛球、网球运动,要找场馆,找球伴,游泳倒是可以一个人,但合适的游泳馆难找,另外还要担心鼻子眼睛会不会过敏,总之,别的运动总是感觉声势浩大,往往还在收拾衣服鞋子的时候,就开始打退堂鼓了。
走路,谁不会呀,只要真的想动,站起来就算开始了,哪怕在小区默默走个几十圈或是楼道上下爬个几次,都算是很棒的一次记录。
第二就是独自。我是很享受自己世界的人,当戴上耳机,迈开脚步,你就与这个世界相融又相隔,自成一个体系。我相信未来科技再发展下去,适合走路的眼镜或是脑部内存片会出来,这样边走路边刷剧,也成为可能。目前来说,最适合运动的伴侣就是耳机了。
以前,从家里去公司,差不多六公里,步行一小时左右,我会选择差不多一小时左右的专题节目,喜马拉雅上有几档音乐节目我是收藏的,主持人音色好,播出的内容专业,大多是港台音乐专辑的介绍。比如叶蓝怀旧经典,还有风铮的夸克调频,微风往事,都是我听了又听的好节目。感谢它们一直到现在还是免费,真是普通听众的大福利。
对于走路,我一开始就人菜瘾大。每周四晚上,有个环山暴走。我会穿越这个城市的下班高峰,跑去参加。雪霁山庄的山门前集合,绕大蜀山一周到望江路口,大约八点四公里,人家最快的四十五分钟就能到,我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是收尾人员等待的落后分子。
后来也参加过南艳湖暴走,翡翠湖暴走,长线的走过,从中环城到紫蓬山,还有是从大铺头走到三十岗,虽然也算体验了这个城市的美好,但现在想来,还是太疯狂了,回想,自己都要骇笑。
后来不发疯了,不会再去做盲目挑战的傻事,但走路这个习惯保持下来了,真的觉得自己精神好了,随意在外吃喝,也不用太担心面目肿胀,甚至2015年那个夏天,我达到史上的最瘦值,看照片锁骨突出,脸也瘦削了。
那会安步当车,动不动就从卫岗走到北一环。晚上饭局结束,哪怕十点了,我还能从万象城走回家,两个多小时里,耳机里放的是中国诗词大会,边走边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瑰丽美好,丝毫不觉辛苦。
微信运动里,我总是霸占朋友圈第一的那个。微信曾给我总结出那一年走了86个马拉松,惹出朋友们一片惊呼。
有个朋友说她老公要加我微信好友,当下惴惴,盘算有哪些秘密不能说,谁知人家也是步行达人,加好友不过是为了在微信步数上一比高低,不由哑然失笑。
现在,我对走路的步数已无执念,甚至关了朋友圈的微信运动,别人看不到我具体的步数。每次看到占据榜首的动辄四五万步的朋友,还是会由衷感叹,疯狂的感觉真好呀!
以漫步热爱一座城市
◎钱红丽
与朋友去市中心图书城办完事出来,由于车泊在了红星路,我们一路穿街走巷,二十年前初来合肥的情境放电影一样。朋友送我回市郊,特意拐上环城河畔的密荫里,当到达赤阑桥路段,我仍记得哪里有两株野木瓜树,哪里有一棵歪脖子树,单位旧址门前的老咖啡馆尚在。
二十年前,真是可以随时起飞的日子。单位坐落于环城河畔——也是这座城市最古气最有静气的一条路。每临周五开完编前会,下一周策划部署妥当后,我们几个单身女同事鸟一样雀跃着窜出大门,嘻嘻哈哈沿着环城路漫游,嘴馋了,趁隙去附近的“大老刘”吃一份鸭杂粉丝。核心主题奔赴红星路,一家一家小店逛过去,摸摸捏捏试试,无事一身轻,不曾有什么明确目的,就是纯粹走一走。红星路尽头有一小食店,鸡汤灌包滋味殊异。年轻时饿得快,热气泡天中站定,买几只包子垫垫肚子。
彼时报纸版面特别多,动不动一百个,个把月攒出十余斤,卖给收破烂的老人,拿一小本子记记账,约莫三四个月,攒下的钱足以去商之都隔壁的海皇阁啜一顿老鸭汤。资金有限,就不带男同事们了,谁叫我们馋呢?将炖得稀烂的鸭肉悉数吃掉,剩下一钵油汪汪的好汤,再端去后厨,下一斤手擀面,叽叽喳喳中盛满面,一个不注意,手上一滑,碗盏呱唧一声,跌大理石地上稀碎,众人哈哈哈,那一个再接再厉重新拿一只碗,继续盛面。吃饱出得门来,早已华灯初上,依然不想回家,继续逛……一群年轻的身体里,何以藏着那么多的精力,一点不觉累?
确乎神仙日子。到了周六周日,浑身的劲依然无处使完,唯余出门消耗这一途。我的活动范围不限于环城河畔,大多冲着好奇的地名而去,梨花巷、四姑娘巷……但凡充满诗性的街巷名字,没有抵达不了的。对一座城市的好奇,全部仰仗着脚力。
每临秋季,当环城河畔的芙蓉临水而绽,高耸入云的水杉针叶渐黄,人行其中,宛在深山的梦幻感——过赤阑桥往西,经过稻香楼宾馆区域,再往前,便是黑池坝,累是有点儿累了,歇歇呗,但也不闲着。临河有一广场,做小生意的,铺开一只硕大无朋的充气塑料鱼缸,充满气,再灌半缸水,放下无数小鱼苗,有的身长仅仅一厘米,吸引孩子们钓鱼。十分钟十块钱。有一次,我匪夷所思加入进去——半蹲于塑料鱼缸前,聚精会神垂钓,许是心不比孩子们静,总想着十分钟快要到了吧,人一焦躁,气必不稳,到末了,一条鱼也未钓上,气急败坏,心有不甘,再续十分钟……一旁的孩子们摒神静气,小鱼儿一条条排着队咬钩,小塑料桶里早已游弋着十余条小鱼了,我这个大人的小桶里空空如也。
二十年往矣,当忆及那啼笑皆非的一幕,当真恍如隔世了。自孩子降临,整整十四年,不曾去过一次环城河畔那一带漫步了。现在去的最多的地方,万象城负一层超市,急匆匆赶往海鲜冷柜,对着琳琅满目的海鱼段,心里反复盘算到底是850克的划算,还是350克的划算,思忖半天,总是比不出高下,不得不掏出手机,点开计算器。飞速结完账,目不斜视搭乘手扶电梯冲出负一层……身边不时闪过年轻女孩们的倩影,她们三五成群结伴穿梭——最潮的衣裙,小腰盈盈一握,纤纤长腿,低跟小黑皮鞋,当真是冰肌玉骨啊,窄小的超短百褶裙,衬得一个个背影,真真乍出水的亭亭小荷……十余年光阴的磨砺,将我与她们完全隔开。我与她们,到底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我们当年城市漫步时,商业确乎不曾发达,不比如今一座万象城,便能承包下所有的娱乐,冬日不冻,酷暑不热。今年春上的一个周末,例行的超市采购完毕,当拎着大袋小袋食品穿过万象城中庭,自奈雪、喜茶、瑞幸鱼贯而过,匆匆扫一眼,里面卡座全被年轻人坐满,人实在多得要溢出,后来的,选择露天卡座,女孩娴雅地抿一小口蛋糕,或者双肘抵于桌前捧着下巴放空。天上正飘着一点细雪,彻骨的寒。一小伙一边呷咖啡,一边紧紧西装的领子,是真冷啊。旁边还有一群男孩女孩,正在细雪下排队,领一支红玫瑰——当日情人节。面对此情此景,怀着对于肉丝袜女孩膝盖冻坏了的揪心,裹着长及脚踝的羽绒衣的我发了一条微博——难道她们不冷吗?不多久,一位外省网友前来纠正,那并非一条简单的肉丝袜,实则是一种有着高科技含量的毛绒袜子,保暖而美。
啊,时代到底不同了。二十年前,当年轻的我们漫步城市时,尚无这些高端饮品小店。当年的我们在红星路逛饿了,不是一份凉皮,便是一碗鸡汤馄饨,哪里有如此高端上档次的小店供我们歇脚?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