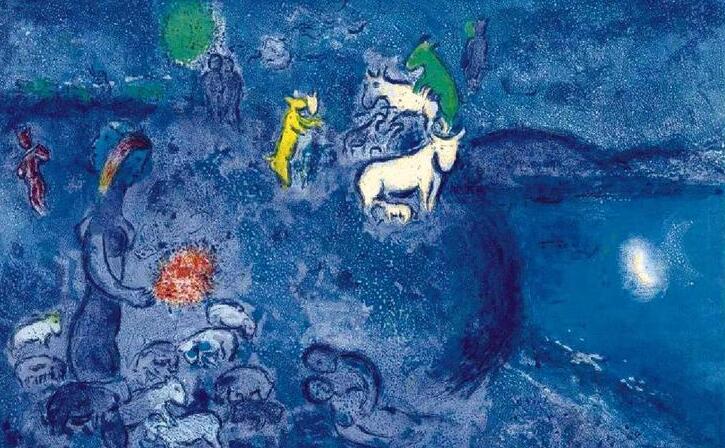·天风
时间是跳跃着前进的,仿佛丛林中的一只兔子。我这样想,靠窗坐下,塞上耳机。这是北京409路公交车,它的终点站是阜成门内大街,那里有鲁迅故居,有鲁迅亲植的白丁香和亲手挖凿的水井。耳机里传出的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即《D大调第五号大提琴奏鸣曲》。我知道,继续往下听,作品将依次是大提琴奏鸣曲第四号、第三号、第二号和第一号。当初是按照这五首曲子创作的先后顺序下载的,但每次听它们,还是喜欢从后面往前听。
贝多芬的这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分别创作于1796年、1808年和1815年,刚好处于他艺术创作生涯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创作的时间跨度足够明显。这其间,年轻的贝多芬应该像任何一个年轻人那样,经历了该经历的事情,同时也经历了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一场革命发生了,一些音乐语言开始注意技巧,往大处说,是这样具有威严气氛,然而一个人走过的四季,波恩小巷,或者令人向往的维也纳,晨曦和薄暮,听力衰退导致的性格变化,资助者去世,从音乐会退出的不得已……无法具体到细节的过程,无法再次听到的风或者雨声,一些醒来即刻忘却的梦,一个人一生中该经历的细微部分,一直在改变一个人。
关于一个人曾经的存在,我似乎只能想象到这个程度,如果再往细处,说不定会成为杜撰。此时正是四月末,杨花迷离,雾霾后的阳光有些温暖,似乎不真实。槐树将形状不一的大团阴影铺到人行道和白色围栏上,细看去,不是斑驳的树阴在摇曳,而是地面和栏杆在轻微晃动。蔷薇从围栏中探出花朵来,月季也是,玫红、浅黄、莹白。行人下去,又有人上来,车子走走停停。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和里赫特的钢琴并不理睬这些,他们的对话一直在进行。那些对话有时激情澎湃,难以抑制,有时又像一支燃尽的蜡烛,安静下来,但安静并不表示平静。一些喋喋不休,一些小倾诉,一些幽叹,也有一些快乐和英气蓬勃。在那里,当我试图将自己置换成钢琴时,我听见大提琴靠着椅子扶手在絮语,而当我将自己置换成大提琴时,我又听见钢琴蹲在我膝前细细讲述。
这样一边听,一边扭头向外看时,我发现街头的人都在杨花中减慢了行进的速度,仿佛空气和阳光也是一种阻力。而这慢下来的速度,又一点一点将人变老。我甚至看见从蔷薇花下走过的人,他鬓间的白发根根分明。我想细瞅他的脸,但他的面容模糊,他似乎是很久前我熟识的人,又似乎是,我新近才认识。我将视线往回收,便又看到玻璃窗上的我的脸,她也已经老了,眼角裹着皱纹。但皱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似乎已经历了许多,再没有什么经历比原先的经历更加新鲜。时间将他们都变老了,而我竟忘记了对他们温柔相待,我早该原谅不肯原谅的人和不肯原谅的自己,我也应该早一些明白这道理。这样想,一时涌上感伤无数。
如果按顺序,从第一首往后听,会怎样呢。贝多芬早期的第一号作品中,时间似乎并没有显现出它的残酷。那时的钢琴有阳光的热情和简洁,那时的大提琴,尽管带点哀伤,更多的是亲切明朗。但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我听了他晚期的弦乐四重奏之后吧,我已经无法将另一个贝多芬遗忘。当我再回过头来听这个作品时,竟然将第一乐章中那个优美的旋律误解成一次华丽转身,说转身前怎样无耐,转身怎样不得已,转身后隐忍中怎样潜藏激愤。
我总是这样先入为主,将晚期贝多芬的影子带到他年轻的时候去,我也总是,要将自己偏颇的私人经验,强加给旋律。如此无可救药地陷进去,有时候,我听到的,也就只是自己了。然而这有什么不妥吗。当我不再被音乐的形式所左右,不再被一个记载的构思所套牢,当我从一个光线迷蒙或者风声渐起的现实滑进一个音乐世界,看到所有的具体化解为零,所有记忆再不需要文字作依托时,还有什么需要犹疑呢。
也许抛掉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复杂和矛盾,抹掉时间留给我自己的痕迹,只是单纯地,从音乐本身去听,或许能听出时光渐次给予他的沉思,以及曲式构思和表现力方面臻于炉火纯青的过程。但我还是喜欢从他的晚期听到中期,再到早期。这种返老还童的逆时光,总比慢慢得来的遍体鳞伤更残酷。
【橙美文】时光的痕迹
安徽商报
张雪子
2023-11-20 10:11:13
·天风
时间是跳跃着前进的,仿佛丛林中的一只兔子。我这样想,靠窗坐下,塞上耳机。这是北京409路公交车,它的终点站是阜成门内大街,那里有鲁迅故居,有鲁迅亲植的白丁香和亲手挖凿的水井。耳机里传出的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即《D大调第五号大提琴奏鸣曲》。我知道,继续往下听,作品将依次是大提琴奏鸣曲第四号、第三号、第二号和第一号。当初是按照这五首曲子创作的先后顺序下载的,但每次听它们,还是喜欢从后面往前听。
贝多芬的这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分别创作于1796年、1808年和1815年,刚好处于他艺术创作生涯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创作的时间跨度足够明显。这其间,年轻的贝多芬应该像任何一个年轻人那样,经历了该经历的事情,同时也经历了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一场革命发生了,一些音乐语言开始注意技巧,往大处说,是这样具有威严气氛,然而一个人走过的四季,波恩小巷,或者令人向往的维也纳,晨曦和薄暮,听力衰退导致的性格变化,资助者去世,从音乐会退出的不得已……无法具体到细节的过程,无法再次听到的风或者雨声,一些醒来即刻忘却的梦,一个人一生中该经历的细微部分,一直在改变一个人。
关于一个人曾经的存在,我似乎只能想象到这个程度,如果再往细处,说不定会成为杜撰。此时正是四月末,杨花迷离,雾霾后的阳光有些温暖,似乎不真实。槐树将形状不一的大团阴影铺到人行道和白色围栏上,细看去,不是斑驳的树阴在摇曳,而是地面和栏杆在轻微晃动。蔷薇从围栏中探出花朵来,月季也是,玫红、浅黄、莹白。行人下去,又有人上来,车子走走停停。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和里赫特的钢琴并不理睬这些,他们的对话一直在进行。那些对话有时激情澎湃,难以抑制,有时又像一支燃尽的蜡烛,安静下来,但安静并不表示平静。一些喋喋不休,一些小倾诉,一些幽叹,也有一些快乐和英气蓬勃。在那里,当我试图将自己置换成钢琴时,我听见大提琴靠着椅子扶手在絮语,而当我将自己置换成大提琴时,我又听见钢琴蹲在我膝前细细讲述。
这样一边听,一边扭头向外看时,我发现街头的人都在杨花中减慢了行进的速度,仿佛空气和阳光也是一种阻力。而这慢下来的速度,又一点一点将人变老。我甚至看见从蔷薇花下走过的人,他鬓间的白发根根分明。我想细瞅他的脸,但他的面容模糊,他似乎是很久前我熟识的人,又似乎是,我新近才认识。我将视线往回收,便又看到玻璃窗上的我的脸,她也已经老了,眼角裹着皱纹。但皱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似乎已经历了许多,再没有什么经历比原先的经历更加新鲜。时间将他们都变老了,而我竟忘记了对他们温柔相待,我早该原谅不肯原谅的人和不肯原谅的自己,我也应该早一些明白这道理。这样想,一时涌上感伤无数。
如果按顺序,从第一首往后听,会怎样呢。贝多芬早期的第一号作品中,时间似乎并没有显现出它的残酷。那时的钢琴有阳光的热情和简洁,那时的大提琴,尽管带点哀伤,更多的是亲切明朗。但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我听了他晚期的弦乐四重奏之后吧,我已经无法将另一个贝多芬遗忘。当我再回过头来听这个作品时,竟然将第一乐章中那个优美的旋律误解成一次华丽转身,说转身前怎样无耐,转身怎样不得已,转身后隐忍中怎样潜藏激愤。
我总是这样先入为主,将晚期贝多芬的影子带到他年轻的时候去,我也总是,要将自己偏颇的私人经验,强加给旋律。如此无可救药地陷进去,有时候,我听到的,也就只是自己了。然而这有什么不妥吗。当我不再被音乐的形式所左右,不再被一个记载的构思所套牢,当我从一个光线迷蒙或者风声渐起的现实滑进一个音乐世界,看到所有的具体化解为零,所有记忆再不需要文字作依托时,还有什么需要犹疑呢。
也许抛掉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复杂和矛盾,抹掉时间留给我自己的痕迹,只是单纯地,从音乐本身去听,或许能听出时光渐次给予他的沉思,以及曲式构思和表现力方面臻于炉火纯青的过程。但我还是喜欢从他的晚期听到中期,再到早期。这种返老还童的逆时光,总比慢慢得来的遍体鳞伤更残酷。
·天风时间是跳跃着前进的,仿佛丛林中的一只兔子。我这样想,靠窗坐下,塞上耳机。这是北京409路公交车,它的终点站是阜成门内大街,那里有鲁迅故居,有鲁迅亲植的白丁香和亲手挖凿的水井。耳机里传出的是贝多芬最后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即《D大调第五号大提琴奏鸣曲》。我知道,继续往下听,作品将依次是大提琴奏鸣曲第四号、第三号、第二号和第一号。当初是按照这五首曲子创作的先后顺序下载的,但每次听它们,还是喜欢从后面往前听。贝多芬的这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分别创作于1796年、1808年和1815年,刚好处于他艺术创作生涯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创作的时间跨度足够明显。这其间,年轻的贝多芬应该像任何一个年轻人那样,经历了该经历的事情,同时也经历了别人不曾经历的事情。一场革命发生了,一些音乐语言开始注意技巧,往大处说,是这样具有威严气氛,然而一个人走过的四季,波恩小巷,或者令人向往的维也纳,晨曦和薄暮,听力衰退导致的性格变化,资助者去世,从音乐会退出的不得已……无法具体到细节的过程,无法再次听到的风或者雨声,一些醒来即刻忘却的梦,一个人一生中该经历的细微部分,一直在改变一个人。关于一个人曾经的存在,我似乎只能想象到这个程度,如果再往细处,说不定会成为杜撰。此时正是四月末,杨花迷离,雾霾后的阳光有些温暖,似乎不真实。槐树将形状不一的大团阴影铺到人行道和白色围栏上,细看去,不是斑驳的树阴在摇曳,而是地面和栏杆在轻微晃动。蔷薇从围栏中探出花朵来,月季也是,玫红、浅黄、莹白。行人下去,又有人上来,车子走走停停。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大提琴和里赫特的钢琴并不理睬这些,他们的对话一直在进行。那些对话有时激情澎湃,难以抑制,有时又像一支燃尽的蜡烛,安静下来,但安静并不表示平静。一些喋喋不休,一些小倾诉,一些幽叹,也有一些快乐和英气蓬勃。在那里,当我试图将自己置换成钢琴时,我听见大提琴靠着椅子扶手在絮语,而当我将自己置换成大提琴时,我又听见钢琴蹲在我膝前细细讲述。这样一边听,一边扭头向外看时,我发现街头的人都在杨花中减慢了行进的速度,仿佛空气和阳光也是一种阻力。而这慢下来的速度,又一点一点将人变老。我甚至看见从蔷薇花下走过的人,他鬓间的白发根根分明。我想细瞅他的脸,但他的面容模糊,他似乎是很久前我熟识的人,又似乎是,我新近才认识。我将视线往回收,便又看到玻璃窗上的我的脸,她也已经老了,眼角裹着皱纹。但皱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似乎已经历了许多,再没有什么经历比原先的经历更加新鲜。时间将他们都变老了,而我竟忘记了对他们温柔相待,我早该原谅不肯原谅的人和不肯原谅的自己,我也应该早一些明白这道理。这样想,一时涌上感伤无数。如果按顺序,从第一首往后听,会怎样呢。贝多芬早期的第一号作品中,时间似乎并没有显现出它的残酷。那时的钢琴有阳光的热情和简洁,那时的大提琴,尽管带点哀伤,更多的是亲切明朗。但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我听了他晚期的弦乐四重奏之后吧,我已经无法将另一个贝多芬遗忘。当我再回过头来听这个作品时,竟然将第一乐章中那个优美的旋律误解成一次华丽转身,说转身前怎样无耐,转身怎样不得已,转身后隐忍中怎样潜藏激愤。我总是这样先入为主,将晚期贝多芬的影子带到他年轻的时候去,我也总是,要将自己偏颇的私人经验,强加给旋律。如此无可救药地陷进去,有时候,我听到的,也就只是自己了。然而这有什么不妥吗。当我不再被音乐的形式所左右,不再被一个记载的构思所套牢,当我从一个光线迷蒙或者风声渐起的现实滑进一个音乐世界,看到所有的具体化解为零,所有记忆再不需要文字作依托时,还有什么需要犹疑呢。也许抛掉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复杂和矛盾,抹掉时间留给我自己的痕迹,只是单纯地,从音乐本身去听,或许能听出时光渐次给予他的沉思,以及曲式构思和表现力方面臻于炉火纯青的过程。但我还是喜欢从他的晚期听到中期,再到早期。这种返老还童的逆时光,总比慢慢得来的遍体鳞伤更残酷。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