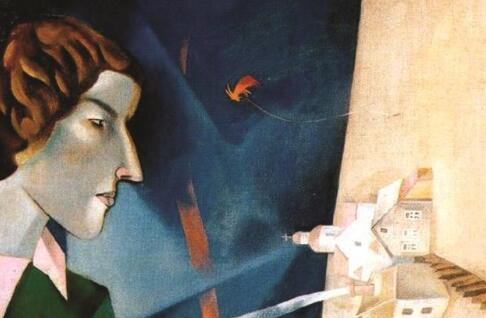中国一共有两个淠史杭。
第一个淠史杭是实体的。始建于1958年,直到1972年主体工程才基本完工,此后一直在完善之中。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用十字镐、独轮车等简单工具,依靠肩挑手抬,以最高日上工人数80万人、累计4亿工时,平均每亩不足40元的国家投资,建成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大灌区。
第二个淠史杭则是数字的。始建于2020年,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它以模拟仿真、AI、云计算等技术构建空间,通过对淠史杭灌区关键数据的精准描述和计算,反馈到物理空间进行诊断、预测、并形成决策,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第一个淠史杭”。
张宝忠是水利部直属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所长,他把第二个淠史杭工程称为第一个淠史杭的“数字化孪生”。
他认为,在淠史杭当前阶段,尽管“数字化灌区”的辅助决策功能还不明朗,但确实已经可以“实现大量繁琐事情的简单化”。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张宝忠同时指出:“淠史杭灌区水源复杂的特点也决定了建设‘数字孪生’灌区的艰巨性和在全国灌区中的示范意义。这种示范意义体现在,在这里建设‘数字孪生’灌区,难度系数是最高的。如果淠史杭都可以,其它灌区就没什么不可以。”
淠史杭工程建设已经65周年了,一个绵延65周年的老牌水利工程为什么要搞“数字孪生”?数字化的背后是什么?它会给农业和城镇用水安全带来怎样的变化?

元新闻记者赴京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所长张宝忠对谈,以下是元新闻与张宝忠的对话:
淠史杭的成绩单
《元新闻》:站在全国的角度看,淠史杭的“数字孪生”做得怎么样?
张宝忠:淠史杭数字(孪生)灌区除建设了包括立体感知、自动控制、支撑保障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外,还搭建了包括供需水预测、水资源配置、供水调度、渠道防汛调度等专业模型,以及渠首枢纽等数字孪生工程,初步实现了灌区“四预”功能(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在全国尚属首例,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淠史杭灌区立体感知网基本建成,汇集监测站点3865处,基本覆盖灌区水源工程、渠首及主要骨干渠道和建筑物,重点支撑了雨情系统、水情监测和供水计量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闸控系统等应用。

《元新闻》:试运行的情况怎么样?“数字孪生”是不是已经在淠史杭发挥作用了?
张宝忠:当然,我举个例子。
受2022年旱情及2023年春季降雨来水持续偏少的影响,2023年春灌前淠史杭灌区上游水库蓄水仅为同期一半。灌区就运用了“水资源配置模型”,动态优化调整供水计划,让栽插水稻面积由初期的632万亩恢复到常年水平的960万亩,为灌区粮食丰产丰收提供有力保障。
淠史杭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过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灌区的数据能够入库、上图。第二阶段,将数据“数字化”,并采用相关的模型将数据运行起来,为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第三阶段,智能化和智慧化,用AI来替代人的计算和决策。淠史杭目前大概处于第二个阶段。
全新的挑战
《元新闻》:一个水利工程或者灌区运行了几十年了,可能已经很稳定了,为什么还要搞数字化?
张宝忠:这背后有一个大的逻辑就是,灌区功能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大中型灌区是保障国家粮食生产的主战场,中国正在推动优先将大中型灌区建成高标准农田。在实践中更关注水源到田间的衔接问题。另一方面,以前灌区供水一直以农业为主,现在变成了“城镇供水、生态供水和安全饮水”并重。几十年前,很难预料淠史杭旁边的合肥会成长为千万人口的城市,有预测说2035年合肥的城市人口将超过1300万人。因此,这种变化伴随城镇化的进程加快是十分剧烈的,水资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
与农业灌溉不同,城市供水面临两个更突出的问题:水的保证率要求很高,而且水质要求也很高。水质检测也在“数字灌区”的范畴之内。
此外,灌区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也在加剧,社会对于水资源调控能力的要求进入了新阶段,要求是“精细化调控”。
举个例子,合肥一带的农村,当地农民工作日在外地务工,只有周末回家;但如果他周末“要水”,到周一水才会来,但周一他又得去打工,这就会出现矛盾。
这实际上都给灌区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一直以来,灌区运行管理仍以传统方式为主,自动化用水测量设施配套不够,闸站智能化控制程度不高,网络覆盖程度不广,灌区供需水、配置调度的测算仍以历史经验估算为主,难以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与科学调度。
所以,“数字孪生”迫在眉睫。它最核心的功效就是“四预”,也就是(水利)部里提出的“把不可知的变为知道一些”。本质上就是要将灌区管理调度由以人工、经验为主上升到数字化、智能化的层面,应用一些精细化手段,去提高水效。
淠史杭的启示
《元新闻》:淠史杭的“数字孪生”试点,对全国其它灌区有什么启发?
张宝忠:全国有很多灌区,但各地都不一样。
西北灌区的特点是缺水,有灌溉的地方一片绿油油,没灌溉的地方就是戈壁荒漠。因此,西北灌区更强调灌区生产和节水本身,新疆地区的滴灌设施发展就很快;内蒙古河套灌区的体量与淠史杭相当,但它一直面临着盐碱地和乌兰素海环境治理问题的双重挑战,因此河套灌区采用“一首制”引水工程。
但是在南方,情况又有所不同。比如浙江,当地政府将灌区视为全社会发展统筹的一部分,对水网进行精细化管理,提升水质和综合生产能力。
安徽地处南北之间,淠史杭灌区的特点和南北灌区都不一样。
第一,淠史杭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与内蒙古河套灌区、四川都江堰灌区并称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第二,淠史杭灌区横跨长江、淮河两个流域,它的旱涝特点非常突出。第三,淠史杭灌区的水源复杂程度位于全国第一方阵。淠史杭工程上引大别山区佛子岭、磨子潭、白莲崖、响洪甸、梅山及龙河口6座大型水库之水,下连1200多座中小型水库和21万座塘坝,形成了蓄、引、提相结合的“长藤结瓜”式灌排体系。
成败关键
《元新闻》:公众可能普遍都认为,水利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领域,而“数字孪生”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你怎么看待全国部分大中型灌区在“数字孪生”领域的先行先试?
张宝忠:中央最早提出“智慧水利建设”;紧接着提出“数字中国”;现在“数字孪生”实际上正是“数字化在水利领域的应用”,是“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要迈向现代化,数字化是必经之路。就像数码相机取代了传统的图像式相机一样,既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体现时代的进步。
在水利上,中央大的布局是在流域层面实现“数字孪生”,往下是水网层面实现“数字孪生”,再往下就是水利工程的“数字孪生”。
《元新闻》:大型灌区搞“数字孪生”,您觉得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张宝忠:我的观点,真正要让使用“数字孪生”的灌区人员觉得好用,这一点排第一位。国内有些灌区建设“数字孪生”,过度追求展示画面好看。如果实际功能让位展示功能,最终结果就是不可持续。
现在功能不是问题了,好用是个问题,常用更是个问题。“数字孪生”灌区未来在精度上能够做到哪一步,这个很难预测,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最贴近灌区的实际应用。
“一直以来,我们也在不停引导全国各地的灌区管理部门,先用起来再说。如果全国各大灌区管理局灌溉调度部门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数字孪生’,这个事就成了。”
(记者 常诚 梁巍)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