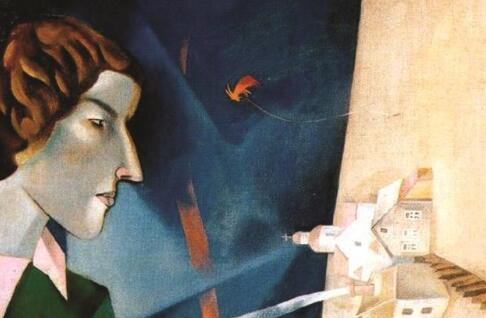滋味的一部分
◎ 张言
三个半小时,从省城回到乡下,人头攒动的集市上,“我”变成了“俺”,寻常日子过成了年。
以前,过了腊月二十,全家老小都巴望着姥爷能回农村老家赶一趟集。
姥爷年轻时,在老家教书,还担任过小镇酒厂的厂长,村里的卖货人好多都是他的学生、同事、亲戚,他每次回老家赶集都能带回最优质的年货。
一来他识货,会买会做;二来姥爷退休工资高,乡里乡亲又都认识,从不在钱上计较,人们觉得这老头和善,有好东西总想留给他。
家里每年都做猪蹄冻,熬蹄冻的做法来自姥爷的父亲,一位曾经的大厨。村里人都吃过姥爷家的这道年菜,杀年猪的人家见到姥爷,少不了问一句:猪蹄要不要给您留着?留着,还跟往年一样。单独留下的猪蹄,尺把长,连带蹄髈下方筋道满瘦的一截,这样就可以在熬制蹄冻时,做出另一道菜——蹄包肉。
猪蹄交到姥爷手上时,表皮白净,肉质新鲜,猪脚缝里都刷得不留一丝杂毛脏皮。卖家这么仔细,跟钱关系不太大,更多的是人情,这份人情也不过是小时候跟着姥爷识过几个字,吃过几顿饭。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被人记在心里久了,便成了人情。姥爷嘴上说着,都是过去的事了,钱该收要收。可心里高兴,这些人情,让他觉得一辈子没白活。
国鸡表叔每年农闲都会去一趟远嫁新疆的老姑家,除了探望最疼爱他的老姑,还会带回五六麻袋葡萄干。葡萄干是老姑家自己晒的,不打药不上色,他习惯将摊位摆在小学门口的老柳树底下,十里八乡的老主顾自会去那里寻他。若是生意好,葡萄干卖得快,时间又来得及,国鸡表叔会让新疆的表弟再发一次货。
他唤姥爷一声大伯,把一布袋黑色细长的葡萄干放进姥爷菜筐里,葡萄干是送的,不要钱,那是他老姑特意给姥爷留的,姥爷跟他家老一辈是姑舅表亲。
国鸡表叔年前忙这一阵儿,能挣够他全年的烟酒茶钱。老有人怂恿他在街上租个房子专门售卖新疆葡萄干、大枣,可他总觉得,庄稼人还是得种庄稼,铺子始终没开。
村子毗邻河南,沿着一条小路,骑车十五分钟就能到河南境地,村里有不少河南嫁过来的媳妇。有位老婶子,她娘家在河南开糕点铺子,蜜三刀、梅豆角、羊角蜜、枣泥酥是她家的招牌。老婶子天一冷便回娘家帮忙,临过年回来时,各色点心堆满一整车。
她直接拉到集上卖,整车糕点一会儿工夫被抢空。她家做的羊角蜜特别好吃,外皮有种水盈盈的口感,薄薄面皮中间好似铺了一层糖水,皮里面的糖浆半凝,晶亮透明,清甜润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甜食。
姥爷每年都提前嘱咐她留十几包,可她每年都没留够数过,最多五六包。后来,老婶子去世,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羊角蜜。
现在过年,大多看图片视频采购物品,虽方便,但少了与人、与有形实物的交流,那个带领食物闯进你世界的人,本身也是滋味的一部分,如今全被摘了出去,不免有些乏味。
收到一张电子红包封面
◎风举荷
上周末,朋友邀约家宴,途经某大型超市,便想着买点伴手礼。
一推开厚重门帘,刘德华那首《恭喜发财》震耳欲聋,果然刘先生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已解冻95%”。
本想买点水果,根本不用费劲爬二楼。收银台边高高垒砌起各种“红盒子”——从奶粉到麦片,从坚果到膨化,从车厘子到红富士,应有尽有。连收银员都套上花棉夹和花棉裤,连连称赞她们“好喜庆”,大姐笑呵呵的,“超市再不喜庆,就真没过年的味儿了”。
她倒说了句大实话。现在的年味儿确实越来越淡,别说和我童年时相比,就是和十年前相比,自己的心境好像也差了不少呢。
小时候过年最盼望的就是那些平常吃不着的零食,牛肉干、鱼干片、奶糖,现在孩子物质极大丰富,谁还稀罕这个;若说放烟花吧,圣诞和元旦时就已整夜炸亮夜空,放多了还嫌呛人;前几年,很多人都流行春节全家出游,这会儿朋友圈里出门浪的人也越来越少;就是热闹的贺岁电影档,家里电视机都奔100寸去了,宅家看也还凑合……
不知是自己年纪大了才会这样想,还是人类社会越来越原子化,人际链接本来就越来越淡。几年前,我的年货清单里,是一定要备一身“新年战袍”的,毕竟过年回来,老同学老闺蜜们总会见面,谁都想看上去更体面点。现在我是能微信别电话,能电话别见面,宁愿把礼物给您快递到家,也不想跨越半个城市去喝茶——就是觉得好累啊。
心里的年味淡了,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父母老了。
之前坚守传统的主要是他们,每年春节除了洒扫除尘,一定要做些家庭传统菜,比如我婆婆一定要做蛋饺、糖醋熏鱼、肉皮冻、醋拌海蜇头;我母亲一定要炸挂面圆、山芋圆和绿豆圆。现在他们年纪都大了,有心力也没体力,那套复杂的手艺传给我也懒得拾起——啥买不到啊,费那劲干吗!
大约十年前,有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一帮川籍农民工,骑着摩托车跨越几千公里,也要回家过年。寒风中,溅满泥点的车后座绑着蛇皮袋,里面装着为家人精心挑选的礼物。很多人看到那条新闻时湿了眼眶——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的信念。
如今的中国,很多县市通了高铁,很多人家也有了私家车,春运回家不再那么难;如今最“忙年”的,似乎就是各大直播间里的主播们,各种线上年货节,各种机制,你没有需求,也在他们的锣鼓喧天中创造出一点需求来,只是新年礼物再也不用大包小包提回家,全国包邮啊!
说到新年礼物,还真是有点变化。
今年我就定了好几盆年宵花闪送给朋友们,有大花蕙兰、蝴蝶兰、火红冬青……物质欲望逐步满足后,审美成了新消费点。我还买了一大叠洒金斗方,自己画了一些龙年简笔画送给朋友,一人一首专属打油诗,大家倒也很欢喜,毕竟独一无二嘛。
自己家里是买了一大堆需手工制作的龙年工艺品,比如纸龙、红灯笼、新年抱抱桶这些,等着放寒假了,和娃一起完成。还买了红纸、毛笔和一得阁的上好墨汁,打算鼓动老父亲重操旧业,他年轻时是为十里八乡写春联的青年才俊,现在没了老乡需求,给家里的两门三户写写春联,过过瘾也很不错。
对了,昨天我还收到一份特殊的“年货”,是一个插画师送给我的电子红包封面,是她亲自画的一条粉红色大龙和小粉兔在做交接仪式,甚为别致!
“岁登通蜡祭,酒熟醵村翁……村村闻赛鼓,又了一年中。”明代诗人李先芳的《腊日》,描写了人们争相购买新熟酒的景象,还有街头巷尾的赛鼓声,烘托出腊日里的热闹与祥和。年味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年货备的不尽相同,但只要参与“忙年”之中,就不会忘记,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
贴年画过大年
◎陈裕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小孩小孩你别闹,过了腊八买鞭炮……”每逢腊月,总会想起这首童谣,儿时过年的场景带着岁月的斑驳,氤氲而至。在为年而忙碌中,买年画最是难忘。
那会儿,流行贴年画过大年。
三里地外镇上的农贸市场,过了腊八逐渐热闹起来。年画是其中的风景之一。那时市场是露天的,所有的年货都自行摆放。商贩们各行其道,板凳、椅子、木板、铁架子都为年货安置个处所,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年画或铺于地上,或挂在铁丝网上,或搭在桌子上,一张张靓丽的色彩,泛着光亮,煞是好看。
年画的种类可真不少。有喜乐型,年年有余、多子多福;有风采型,古装武将、现代英雄人物;有四季风物,各种花草各式器具。每一种年画烈烈生艳,每一幅年画饱满圆润,让人流连。看年画,赏画景,入眼更入心。
除了鞭炮的摊位外,年画的商贩点前人最多,男女老少各人等,挑挑选选,热闹非凡。很多人早早来看年画,生怕好的年画被人挑走。人挤人的场面有点壮观。不时的,两个人看上同一幅年画,争辩了几句,忙碌的老板赶紧拿出存货来解围,大家相视而笑又是一团和气。
我们一家人也来选年画。我喜欢山水图,大自然的风景最纯净。弟弟喜欢看武打电影,他看中英姿飒爽的岳飞骑马图。妹妹喜欢花草,她挑了一幅梅兰竹菊四君子。我们各有所爱,皆大欢喜。
回到家里,年画还得珍藏起来,过了小年才可贴到墙上。每幅年画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早已分配好各自年画的领地。我的山水年画在东墙,弟弟俊郎岳飞的年画在北墙,妹妹的四君子在门旁。每一处年画贴处都是自己来打扫。扫尘时,我们特别注重年画位置的干净。那会的墙面都要糊上一层白纸,我们自己动手,糊得分外仔细。
糊好白纸后,待浆糊干透,量好年画的尺寸,目测年画的方位。一张张年画贴起来,我们兄妹三人协同合作,相互配合。
画贴好后,屋子里顿时焕然一新。白色的墙,多彩的年画,喜气洋洋的笑脸,新年的味道逐渐丰盈。躺在火炕上,端详着崭新的年画,越看心里越美。
去邻居家串门时,我最喜欢看年画了。每家的年画风格迥异,但都欣欣向荣。年画既是一种装饰,也是一种愿景,为乡村简朴的生活增添了岁月的光彩。一年又一年,年画的造型和色彩也不断变换着,但无论怎样改变样式,都是对新年的无限希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贴年画过大年,是旧时年味风情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篇章,也是乡村时光中的一道流行风景线。不管人生走过多少路程,那些年在乡村的生活,在乡村度过的新年,注定会成为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片断,给予我温情的怀念。
养了几尾鱼
◎钱红丽
腊八以后,总要买回几尾活鱼养养,年年不辍,似乎形成了肌肉记忆。这几尾鱼,构成了我们家最不可或缺的核心年货。
到底说不清究竟为了什么,或许受了我妈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爸一生嗜好食鱼,记忆里,年年春节,我们家都会养一些活鱼,随食随宰。另一层意思,也正契合着“年年有余”的古老传统。
我们父辈这一代,作为物质过度穷乏的一代,曾挨饿过的他们,其人生愿望里,重中之重的一项,无非年有余粮。家家户户年三十的餐桌上,照旧有一盘碗头鱼,不能动箸,同样象征“年年有余”。
腊八当日,一样将年鱼买回。自小池塘中哼哧哼哧拎回半桶天然水,再掺半桶自来水,无须制氧。来自水库之中的鲫鱼,大小不等,一拃长的,半斤重的,三四尾,迁来桶中安家。
过后几日去菜市,邂逅老人挑来的一群野生乌鳢,殊为难得,忍不住又买两条,盈盈一尺长,扭动着肥胖的暗纹身躯,滑溜溜地汇入桶中,与鲫鱼结伴。
闲来无事,喜欢蹲在桶畔,静观游鱼。日升月落,几日处下来,彼此渐熟,它们大抵放下戒心,不再提防。
刚买回时,鱼的眼神非常的不落定,是惊慌的,带有仓惶之色,惴惴不安的,一日日地捱着过……到末了,它们发现这眼前的巨大怪物无意于伤害自己,便也从容起来,在我家越过越舒心,眼神变得柔和,宛如春水解冻,是荡漾着的了……
鱼的眼神是真清澈啊,冬月一样凛冽,对你闪电一瞥,一霎时没入水底去,十万春花如梦里。倘若午后,阳光和暖,鲫鱼们集体浮上桶面,吹个呼哨吐几串圆圆的小白泡泡,逗我玩。我也吹声口哨,以示回应。颇为害羞的它们,瞥我一眼,迅速没入水中,留下一线青脊隐隐现现。玩得兴起,我偶尔拿脚尖轻叩一下桶壁,小精灵们吓一大跳,急速游窜,许是太过紧张,相互撞在了一起,卷起尺高的水花,慢慢地,又复归于宁静。翌日,当我故技重施,冷不丁又踢一脚桶壁,再也无鱼理睬,一尾尾好整以暇游弋自如的样子,偶尔有一尾各色的,将头探出水面,啜起小嘴儿,白我一眼。怪聪明的呢。
整一个腊月岁尾,不时有爆竹于远方炸响后的隆隆之声,反衬于心间,不免有急景凋年之感,一颗心难免慌慌的,不太静得下来。除了去居所附近的荒坡晒晒太阳以外,我总喜欢蹲在水桶边,与鱼作伴,久之,一任窗外北风萧然,一颗心便也沉了底,万物次第目前。
昨日,上露台,蜡梅的寒香阵阵中,养了七八年的黄种月季,绽出第一颗紫芽,令人欣欣然又怡怡然……天空浩瀚蔚蓝,四野八荒,俱成永恒静谧。这平凡的日夜,赠我以年过半百的年纪——接下来,我不知还能迎来几回冬往春来?
这几尾鱼,渐渐地被当成了宝贝,其饮食起居,均为我一人操心照护。三两日,换一次水。脏水舀出半桶,续进半桶净水。脏水拎回家冲入马桶,接半桶自来水晾着,让氯气散去……拎进拎出间,累得气喘吁吁。寒冬里的鱼静气笃定,实则,生命力依然蓬勃,每每换水之时,于桶里上蹿下跳,一蹦三尺高,溅起水花扑你一脸一身。
家里暖气,会导致水温升高缺氧,鱼桶拎去外层露台,一直维持于零度左右。夜来,可观星月。白日,可晒阳。偶尔丢两片绿叶菜进去,过冬不食的它们无心吞吐。阳光正好时,会追逐叶子的影子嬉戏。
乌鳢像极得道高僧,一味潜伏于桶底,不喜不伤,无垢无过,整个腊月俱是静定状态。倘将所有的水倒光,与其劈面相逢,它们才勉强瞄你一眼,稍稍将自己遍布暗纹的肥美身体扭成S型,仅此而已。
无法形容出乌鳢那种眼神,并非空洞无光,而是荒荒漠漠的,深藏另一个广大浩渺宇宙,如若星外来客,叫人琢磨不透。乌鳢这种鱼,最会蓄力,犹如自持内敛之人,情绪一直稳定。
翻过年,像翻过一座山。转眼春来,气温一日高似一日,注定要与这些年鱼惜别。我不信教,但,年龄愈长,愈不忍杀生。这些鱼们的归宿,无非小池塘。小区这一方水域,要比水桶广阔千万倍。
塘水清浅,所有的鱼轰隆一声倒下去,冲击力搅起塘底淤泥,一片青灰,一忽儿,水又变得廓清,乌鳢也好,鲫鱼也好,宛如老僧入定,于原地一动未动。
人鱼之间,原本萍水相逢,谈不上什么舍得舍不得的。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