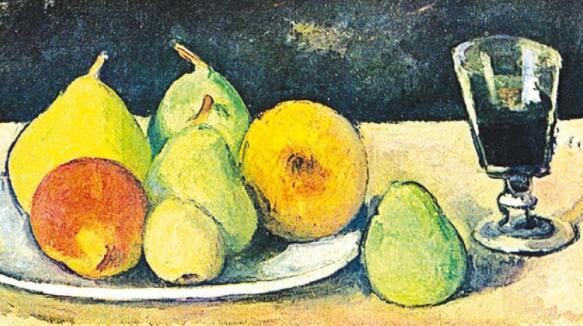时光倒流千年。宋代如果要锁定一个文学地标,肯定是眉州,唐宋八大家,眉山苏氏一家出了三个;要是选一个文化形象大使,不用选,一定是苏轼,华语世界宋代诗文点击率最高。
我老家滁州,三十年前第一次见到琅琊山《醉翁亭记》碑刻,很惊讶碑有一人多高,字比碗口大,每个字像是字帖上抠下来的。欧阳修《醉翁亭记》早会背了,到现场才晓得字是苏轼写的,501个字,刻在两大块石碑正反面。
读书那会儿,文学史上的“欧苏”专指欧阳修、苏轼散文,平实文风与优美文字浑然天成,撬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欧阳修的文和苏轼的字藏在我老家山里,双星闪耀,珠联璧合,老汤原汁吊足了千百年游客的胃口,当时我就想,得去一次眉州,到苏轼老家将书上的“欧苏”问个究竟。
“人生如梦,多情应笑我 ”。三十年后终于来了眉州,住的宾馆离苏轼老宅三公里,过于亢奋,中午午睡没睡着,眼前总是晃动着《醉翁亭记》碑刻的影子,影子里赵孟頫对正刻碑工匠说,苏字“潇洒纵横,外柔内刚,棉里裹铁也!”约定下午两点半去三苏祠,急匆匆赶到楼下,中巴车泊在猛烈的阳光下,竟不见一个人影。原来看错了点,才一点半。五月的眉州,夏天好像提前来了。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出生的老宅,元末改祠堂,明清扩容、増修,现在的三苏祠104亩,比苏轼出生时扩了至少10倍。一进“三苏祠”正门,迎面是飨殿“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对联,上联命名苏氏父子三人,下联则单独为苏轼定位。这父子仨共同身份是“散文”大家,那时候叫“古文”,“三词客”属代称,便于上下联对仗工整;论词的影响力,凭《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三首词,苏轼的词应是父子仨中写得最好的,也是北宋一堆伟大词人中的老大。散文唐宋八大家,千年只有四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欧苏”在三苏祠对联中汇合。
眉山三苏祠“碑亭”里,除了复制的楷书《醉翁亭记》碑刻,第一次见到了苏轼草书碑刻《醉翁亭记》,以前都没听说过。滁州琅琊山里还有一个丰乐亭,名气没醉翁亭大,欧阳修写的《丰乐亭记》,苏轼也题写了碑刻,“三苏祠”里楷书碑刻《丰乐亭记》原样复制,感觉与滁州如出一辙。散落在四面八方的“欧文苏字”,三苏祠里全到齐了。
三苏祠镇馆之宝是《醉翁亭记》宋拓本,2022年1月“吾家东坡”特展上首次亮相,这是国内年份最久、保存最好、离苏轼原版最接近的《醉翁亭记》真迹,如今滁州琅琊山苏轼题写的《醉翁亭记》是明嘉靖重刻,行家能看出跟三苏祠里的宋拓本有些微分别。1091年,滁州太守王诏转弯抹角找苏轼好友刘季孙,专程去请颍州(安徽阜阳)太守苏轼题写《醉翁亭记》,两人一见面,推杯换盏,酒喝多了,苏轼即兴草书一幅,次日酒醒,觉草书不能表达对欧阳修的虔诚与景仰,十天后重写楷书《醉翁亭记》,成了一代楷书经典。草书被刘季孙私藏,转辗九百年,真迹毁于大火,三苏祠草书《醉翁亭记》碑是按明代拓片复刻。苏轼题写《醉翁亭记》时,欧阳修已经去世19年了,按说完全可以不写,但他写了,草书落款中注解是,“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欧苏”是师徒关系,也像是父子关系。1056年主考官欧阳修看了苏轼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相差三十岁的“欧苏”从此成莫逆之交,成铁板一块。
我跟老家的地方志学者做过交流,“欧文苏字”能不能叫“欧苏”, 他说“欧苏”是由口语化而演绎来的文学概念,内涵和外延很宽泛,只要合适,只要恰当,完全可以。由此,“欧苏”在散文共识之外,有了第二层涵义“欧文苏字”。
从眉山回来后,我所有的阅读都聚焦于“欧苏”。在百多万资料的字里行间,“欧苏”当肇始于欧阳修与苏洵,苏洵聪明绝顶,年少贪玩,二十七岁发愤,但为时已晚,两次科考落榜,弃考教子,教出了两个儿子同一年中进士。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跋山涉水赶考京城开封,怀里揣着成都太守张方平写给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推荐信,欧阳修拆信时对这个四川口音浓重的苏洵并没放在眼里,看了他带来的《六国论》《权书》《几策》《衡论》《管仲论》等文章后,大惊失色,称其“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可与刘向、贾谊媲美。从此两个地位悬殊的人成了铁杆,欧阳修推荐苏洵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河北霸州文安县主簿,一个没有学历的人当上了官,这在北宋几乎就是神话。1066年苏洵病逝于京城,欧阳修写了《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一个朝廷的省部级大官为一个县官写墓志铭,关系自是非同一般。欧阳修比苏洵大两岁,同辈人。我看到墓志铭中有这两句,苏文“公卿士大夫争传之”,苏洵称“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与苏洵相见恨晚那一年,苏轼19岁,苏辙17岁,进士还没揭榜。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的隔代忘年交是在苏洵死后。
史实中的“欧苏”显然还包含着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交往与交情。“欧苏”由政治主张、文学观念、人生趣味的无缝对接,拓宽到两个家族的联姻,苏轼长子苏迨中举那一年娶了欧阳修孙女十四娘为妻,“欧苏”结为了儿女亲家。1072年欧阳修去世后,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写得情真意切泪流满面,“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后来苏轼和苏辙分别为欧阳修夫人撰写了祭文和墓志铭。举一个例子,1071年,欧阳修在颍州(安徽阜阳)做太守,苏轼苏辙兄弟俩携家眷,专程去颍州看望垂垂老矣的欧阳修,整整二十天,师生每天泛舟西湖,把酒赋诗,临风作赋,“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颍州杭州都有西湖,苏轼酒喝多了,分辨不出哪个更好。苏轼在《西江月·平山堂》一词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凭吊恩师建扬州平山堂,眼前竟然出现了幻觉。
至此,在文章“欧苏”、文字“欧苏”、家族“欧苏”、姻亲“欧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链接,那就是情感“欧苏”。
佛说,你遇到的人是你今生注定要遇到的。这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是缘分,是量子纠缠。机缘巧合就这样将“欧苏”不可思议地叠加在了一起,1048年欧阳修任扬州太守,1092年苏轼任扬州太守;欧阳修1049年任颍州太守,1091年苏轼任颍州太守,同一地点,同一官职。欧阳修贬官三次,饶州、夷州、滁州;苏轼也被贬三次,黄州、惠州、儋州。欧阳修在朝廷任过礼部尚书、刑部尚书,苏轼也任过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多一个吏部尚书,只干了7个月。至于两人都好喝酒,口无遮拦,文章盖世,恃才傲物,有太多的重叠,即使隔着三十年时空,“欧苏”仍旧相互复制,相互拷贝。
课堂上老师讲授《醉翁亭记》,非要说文中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实在有些牵强,《醉翁亭记》的核心要义是道家和佛家的“无为”与“放下”,是超然物外的自在、自洽、自由与自我,“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乐其乐也”。苏轼不仅效法恩师文风,还赓续了欧阳修远离世俗后的“道法自然”的理想,豪放词《赤壁怀古》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对功利主义人生的否定,人世间的看不透,看不破,一切皆因“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他才有了后来流连山水、把酒临风的潇洒与旷达,“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每到一处,身心更多投入美食、美酒、美景,风靡眉州和全国各地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东坡酒、东坡饼全都缭绕着享受生活、珍爱生命的烟火气息。作为两个因言获罪的文坛大家,他们的文字不仅参政议政,还向一个朝代释放了特立独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苏轼概括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三次流放,而不是朝中当了三次尚书。“文官致政”下的北宋文人,个个都是身上带刺,头上长角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一脉相承最终孵化出了精神性的“欧苏”。
离开眉州三个月后,一个简单而丰富的结论已经出来了,“欧苏”与“苏辛”、“苏黄”放在文学史的同一页中,“欧苏”已全方位突破了文章和诗词歌赋的界限。
(许春樵)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