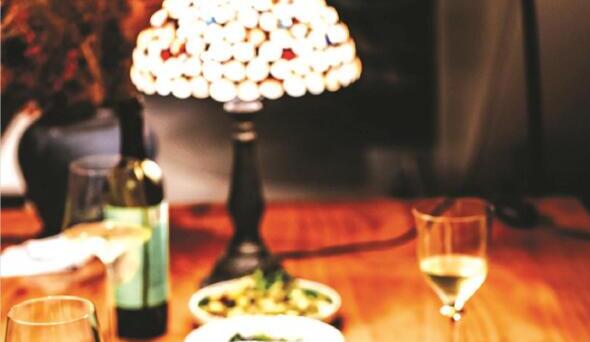近日,有媒体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题目叫《老赖们维权记:为姓氏尊严而战》。
看标题前半句,令人颇为诧异:怎么平时总是“被维权”的老赖们还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了呢?
看标题后半句才恍然大悟,这里的“老赖”应该是指姓赖的人。
正是因为“老赖”有这两层意思,导致一群赖姓人士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维赖”行动,诉求就是:不要再把失信被执行人称为“老赖”,这损害了他们的姓氏尊严。
看了这篇报道,我有两个感受。
一是尊重。“维赖”人士能以合法合规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而且坚持了七年之久,有追求又有毅力,值得尊重。
二是惋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份追求和毅力固然可贵,但是被用在了没有必要的地方,有钻牛角尖的嫌疑。
从语言的特点来看,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都有约定俗成的成分,也都有一些歧义词。歧义词一般是因为同音造成的谐音双关,还有些歧义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失信被执行人和姓赖者都被喊作“老赖”,就是约定俗成的歧义。
语言准确是顺利沟通的前提,那为什么还会有歧义词存在?因为在特定的语境下,交流者并不会混淆歧义,而是默契地在这个语境下去理解,不会多想。
只有两种例外情形:客观上脱离语境孤立理解,或者主观上利用歧义开玩笑。
以报道中的“维赖”者赖一权为例,当别人喊他“老赖”时,双方其实都知道只是喊他的姓,当看到墙上“严厉打击老赖,净化信用环境”的标语时,双方都知道标语中的“老赖”是指失信被执行人,不会混淆。
既然如此,赖姓人士何必要主动把姓赖的“老赖”和欠账的“老赖”绑定在一起呢?四川话中有个词叫“抓屎糊脸”,大意是把不光彩的事硬往自己身上揽。话糙理不糙,窃以为不必。
赖姓人口数在中国排名第98位,约250万赖姓人士占14亿总人口的0.18%。就算所有赖姓人士都上阵,能改变14亿人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吗?就算能,改变这种并无恶意的约定语言,意义何在?
即使赖姓人士对“老赖”这个词维权成功,相关部门郑重其事地规定,失信执行人不可被称为“老赖”,接下来,“赖账”“赖皮”等词还能不能用?赖姓人士是不是还要锲而不舍地维权到底?
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因为头皮上有几处癞疮疤,一开始讳说“癞”和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光”也讳“亮”也讳,到最后连“灯”“烛”都讳了。
假设赖姓人士“维赖”成功,那么人口数排名第七的黄姓是不是要“维黄”?淫秽为什么要叫“黄”、常见的“扫黄”提法是不是伤害了黄姓人士的感情?
曾有网红教授在短视频中普及刑法时,经常以“张三”代指犯罪分子,网友调侃称为“法外狂徒张三”,人口数排名第三的张姓人士是不是应该起诉他?
网络上有个梗叫“隔壁老王”,指代通奸关系中的奸夫,人口数排名第一的王姓人士是不是要团结起来“维王”?
推而广之,因为语言的歧义或泛化而需要维权的人就太多了,尤其是在新词迭出的互联网时代。“你这个老六”,排行第六的人不愿意了;“蚌埠住了”,蚌埠人不愿意了;“渣渣辉”,名字带辉的人不愿意了;打不死的“小强”,名字带强的人不愿意了……
再推而广之,可能还会有一部分姓氏会“被维权”。姓师,凭什么我就得喊你“老师”,你得改姓。姓宫或龚,我一喊就是“老公”,更不行,你必须改姓。
只要愿意埋头寻找,问题无穷无尽,那么,很多与姓名相关的词汇还能正常使用吗?又打算花多少精力来维护各自的“玻璃心”?
假设我姓赖,如果有人正常喊我老赖,我会坦然答应,因为我知道这其中没有歧义。假如有人故意利用老赖的歧义开玩笑,我要么一笑置之,要么就告诉对方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希望下次不要再开了。
报道中,面对“维赖”七年但依然层出不穷的“老赖”,一位赖姓人士表示,除非国家下令他们改姓,否则一直会坚持下去,尽管这可能是一场打不完的“维赖”仗。
好吧,笔者虽然不赞同如此固执的“维赖”之举,但是支持他们“维赖”。就像伏尔泰说的:“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陈卫华)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