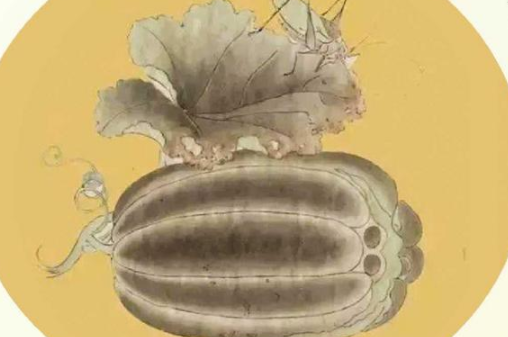2014年,我认识了生活在南海边的几位朋友。之后,跟着他们接近大海。
大海于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我,更像精神中的事物。海在我的表达经验中几乎空白。我时常会想起法国作家古尔蒙的一句话:“天主不是什么人都回答的,大海也是”。
好多次,我们集结于深夜。海在不远处,海风鼓涨我们的衣衫,路灯下一行怪异的影子。夜深寒凉,海的气味和着栀子花香,弥漫在黑暗中。我们安静行走,脚步窸窣急促,像要赶一个隆重的事件。
而大海之上,夜半出海的渔民正开始返航。这种夜色中的劳作带着一种神秘。有一天,我因为好奇泊在海滩上的一条老船,遭到渔民的呵斥。诗人慧谋兄说,渔民自古有讲究,女人不能登船。弗雷泽的《金枝》,煌煌大著中的讲述,关乎生死的时刻,几乎都禁忌女人。重翻《猎人和渔夫的禁忌》一章,“在原始的狩猎和捕鱼之前,几乎都禁绝女人的参与,在某海岛,出海前的男人须要移居别处,不能看妻子一眼,如果不守禁忌,海里的飞鱼必将戳瞎他的眼睛。”
宽厚与啸厉、狂暴与温存,共存于海。为不惊扰大海里的神灵,渔民以约束种种深厚的俗世之爱作为代价。而海的无常,让渔民总是面带忧戚,这种表情世代相传,他们的面庞大都清瘠黧黑、沉默沧桑。
宏大的事物几乎都怀着一种宏大的朴素,大海渐渐清晰的过程,令我震撼。在黄土高原,我常在内心眺望大海,曾无数次想象希腊神话里手持鱼叉乘着金色战车的波塞冬如何飞驰海面。深夜,海存在,却无形,融入茫茫黑色。尽管我几乎能彻夜听到它推波助澜,并在这轰响中想象无数黝黑的浪头如何烈马般追赶。但黎明将至,我想象,神话里那无邪的海豚游来,大海会显出另一派宁静和慈爱。
眼前的一切醒了,天空和大海,露出平静而无涯的灰色,这巨大的空茫,有一刻,让我深感落寞。倏然间,朝霞穿过云隙射下万道光芒,远远近近,构成令人目眩的辉煌。归来的渔民拖船、拉网、收鱼、收网。鲜有人大声说话。大朵大朵海蜇像透明肥厚的花瓣被倾斜在浅滩上,岸边的女人将它们一朵朵抱起,放进篮子。
我的目光几乎还同时追踪着李好,他端着相机,赤脚奔走在各个船上。
海浪无边无际地翻涌。
在表达口舌滋味的汉语词汇中,我以为,甜是暖的母性的可以宠人的,甜加上“蜜”,更是黏糯得缠绵。咸粒像小小的针刺,苦像压在舌头上的木石。
海边长大的李好和渔民这样谈论“甜蜜”。
李好说,刚打回的鱼,在清水里煮了,然后蘸着化开的盐水吃,那个甜蜜呀。
盐是海盐,我见过的,在灰蓝的天空下,一堆堆,碎玉般洁白莹润,捏一撮在手心,能沁出油脂。李好说“甜蜜”时,表情富足得像个孩子,我甚至能听到他下咽涎水的声响。“咸”也是“甜蜜”,那种满身心的喜悦、形而上的幸福。世上的咸,滋味原是有着万千差别。
而我要说的是他的目光——经由他的黑白镜头表达出的“看”。大朵大朵灰云,万道亮白的霞光,海水是有质感的沉重的黑灰汁液,只翻卷的白色浪花显出轻盈,船在逆光中。海天之间,渔人在船头劳作,头上顶着云朵。
那天,我被他的一个镜头打动——鱼儿都已收好,虚空的渔网几乎堆满整个船舱,一个顶着草帽的渔民站在船舷旁睡着了,看不见他的脸,只两只手靠近镜头,疲惫地垂在船舷上。天上依旧铺排着有光泽的灰云,船旁躺着幽暗的海水。镜头充满忧伤的气息,而且确乎因着黑白色度,以一种静默的形式显得更加低沉喑哑。
李好深爱这些他父辈一样的渔民。他的情感都沉沉地压在他的镜头里。他一边怜悯着这样的渔人,一边又怜悯着满海滩打捞回来的鱼儿。鱼和网,人和鱼,船和大海,在他的镜头里对立、冲突,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他说,无序的打捞开始破坏自然法则和秩序,机器的轰鸣搅扰着大海的平静,索取没有止尽,而海永远在沉默、在低处。后来,李好把自己的一个大海主题的摄影展命名为“海在低处”。“海在低处”,有他复杂的隐喻。
低处的海,辽阔无边,尽揽云天,不知是否是这种简约单纯的宏大促成了他对素朴的黑白的喜好?还是大海貌似平静的波澜壮阔启发了他的艺术追求?
以静默制造喧腾,这种放空的哲学如此有效地附着于一些博大而安静的色调上,比如黑、白、灰,以及探照其上的光亮,它们有着相似的气质。我想,这种好意思,从艺术到人生,并非人人能够意会。
我犹记得他照片中的一个反复意象,以及这些意象传达出的焦虑或者忧虑:镜头紧贴地面向上仰视——海滩上人影壮阔,人们摩肩接踵,纷乱的赤脚间,紧挨着镜头,总躺着形形色色的鱼,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像纸张上的感叹号,都圆睁着眼睛。
(习习)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