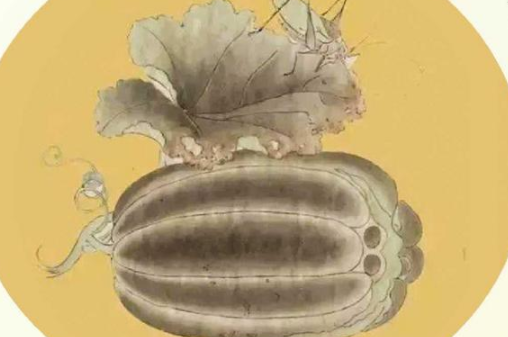读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随笔集《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其中一段文字忍不住多读了几遍:
在被风吹得树干弯曲的白桦树后面,依稀可见远方的群山,层峦叠嶂,一片瓦蓝,交相辉映的天空同样瓦蓝、宽阔,一望无际的河口湾也泛出淡蓝色,浅沙滩上的草开始变黄。在高坡上曾坐落过村庄,有一些房屋还留下火炉、烟筒,拱形木板屋顶,房屋已经下沉。花楸树和稠李树表明这里曾是栅栏围着的房前小花园。村庄淹没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有一条勉强看得出的小道可以通行……
不仅仅是因为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有似曾相识的风物,群山,溪流,灌木丛,白桦树,蓝天下是高坡上的村庄,炊烟寂静,如果是雨后,白云出岫……这段文字惹人回忆的,更多是童年时期的一种阅读体验。
那时在祁连山东段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度过。交通闭塞,信息阻隔,八十年代初的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人外出读书,我是村中上学的为数不多的女孩之一。正是求知如渴的年龄,然而除去教材,除去几本辗转不已的连环画本,再无足够书籍可供阅读。记得一个日光漫漫的暑假,我从幽暗屋角扒出父亲曾经的课本,吹去浮尘,整理干净,有空时就坐在檐下石阶上一页页看。课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忘记,依稀记得有鲁迅的《风波》,附一幅黑白插图:河流、小船、长辫子的男人。或许有另一幅图,九斤老太捏着破芭蕉扇敲着桌凳。一字一字读,却只读得懂一个简单故事。至于江南水乡的风情,以及乌桕树、蒸干菜、独木桥,因为陌生,没激起多少兴趣。也翻出一本残破的描写俄罗斯原野的书籍(现在想来,该是《猎人笔记》或者《林中水滴》之类)读。发黄起皱有烟熏味和尘土味的纸页里,一个辽阔世界逐渐打开。那里季节分明,景物各异。如果是春天,大麻和荨麻发出馨香,矢车菊与铃兰同时开放;夏天,葱茏的黑麦和燕麦泛起涟漪,云雀在田地上空高高低低地叫,灌丛里到处是草莓和蘑菇,高大榛树黑黝黝矗立,树底下是松鼠和雪兔;到了九月,那里的白桦树通身金黄,寒鸦飞来飞去,雾凇在谷底闪耀白光,树丛深处,磨房轧轧地响……
那世界那般熟悉又那般陌生,那般遥远又那般逼近。
很快迷恋起来。一次不会读得太多,薄薄一本书,不能饕餮,得省着读,以打发漫长假日,有时是因为琐碎的家务活等我去做。某个午后,放下书本,拿起镰刀去山上割草。一步步在山路上走,遍野的迷蒙日光仿佛魔法,它将眼前世界与文字里的俄罗斯原野相重叠:宽广无际的蓝天和层叠绵延的群山,夏季风送来远方的清凉与草药芬芳。河水汤汤,白桦生长在山腰,黑魆魆的灌丛在山坡蔓延,路旁的高草下藏着草莓和蘑菇。林间寂静又喧响。松鸦机警,野兔蹦跳,赤狐躲在山冈。如果从荨麻旁经过,得小心翼翼,若稍不留神,荨麻的刺会刺得手指头又疼又痒……仿佛在此处,又似在别处,仿佛是现实,又似在文字的原野里纵横驰骋。
有时候,也会将书中事物与身边事物一一比对。大部分是植物,荨麻、大麻、苦艾、侧金盏花、燕子花,偶尔也有云雀鹞鹰之类。大致都能对得上。譬如荨麻,我们对它的称呼与书里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譬如苦艾,我们称其为苦蒿。也有一些植物,私下认定是它,却无法确认,譬如牛蒡。牛蒡在道路旁胡乱生长,大叶子如象耳招摇,开花,结出小刺猬似的果,人们将其随意称呼。我凭借文字描述和想象,猜测它就是俄罗斯原野上的牛蒡。以至于执拗多年,很多年后,终于得以确定。
那诸般贫瘠的年代,那种偶然获得的阅读是独特的,凄楚,却又瑰丽,迷人。那些文字灵动、活跃,生机勃勃,如野草披拂的小道,逐渐将我同一个遥远的世界相连。我得以走出,并进入一种广漠无际,在那里摸索、兜转,像我在生活中那样,行走山野,采撷种子与植物根茎。我将寻觅所得打包,扛起,返回我在山村的现实,植下它们。没有排异,没有抵触,两个世界竟然彼此补充,我因此很快熟识眼前草木,并得以知晓,在遥远寒凉的北方,它们同样生生不息。
【橙美文】最早的阅读
安徽商报
张雪子
2023-06-19 10:11:01
读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随笔集《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其中一段文字忍不住多读了几遍:
在被风吹得树干弯曲的白桦树后面,依稀可见远方的群山,层峦叠嶂,一片瓦蓝,交相辉映的天空同样瓦蓝、宽阔,一望无际的河口湾也泛出淡蓝色,浅沙滩上的草开始变黄。在高坡上曾坐落过村庄,有一些房屋还留下火炉、烟筒,拱形木板屋顶,房屋已经下沉。花楸树和稠李树表明这里曾是栅栏围着的房前小花园。村庄淹没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有一条勉强看得出的小道可以通行……
不仅仅是因为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有似曾相识的风物,群山,溪流,灌木丛,白桦树,蓝天下是高坡上的村庄,炊烟寂静,如果是雨后,白云出岫……这段文字惹人回忆的,更多是童年时期的一种阅读体验。
那时在祁连山东段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度过。交通闭塞,信息阻隔,八十年代初的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人外出读书,我是村中上学的为数不多的女孩之一。正是求知如渴的年龄,然而除去教材,除去几本辗转不已的连环画本,再无足够书籍可供阅读。记得一个日光漫漫的暑假,我从幽暗屋角扒出父亲曾经的课本,吹去浮尘,整理干净,有空时就坐在檐下石阶上一页页看。课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忘记,依稀记得有鲁迅的《风波》,附一幅黑白插图:河流、小船、长辫子的男人。或许有另一幅图,九斤老太捏着破芭蕉扇敲着桌凳。一字一字读,却只读得懂一个简单故事。至于江南水乡的风情,以及乌桕树、蒸干菜、独木桥,因为陌生,没激起多少兴趣。也翻出一本残破的描写俄罗斯原野的书籍(现在想来,该是《猎人笔记》或者《林中水滴》之类)读。发黄起皱有烟熏味和尘土味的纸页里,一个辽阔世界逐渐打开。那里季节分明,景物各异。如果是春天,大麻和荨麻发出馨香,矢车菊与铃兰同时开放;夏天,葱茏的黑麦和燕麦泛起涟漪,云雀在田地上空高高低低地叫,灌丛里到处是草莓和蘑菇,高大榛树黑黝黝矗立,树底下是松鼠和雪兔;到了九月,那里的白桦树通身金黄,寒鸦飞来飞去,雾凇在谷底闪耀白光,树丛深处,磨房轧轧地响……
那世界那般熟悉又那般陌生,那般遥远又那般逼近。
很快迷恋起来。一次不会读得太多,薄薄一本书,不能饕餮,得省着读,以打发漫长假日,有时是因为琐碎的家务活等我去做。某个午后,放下书本,拿起镰刀去山上割草。一步步在山路上走,遍野的迷蒙日光仿佛魔法,它将眼前世界与文字里的俄罗斯原野相重叠:宽广无际的蓝天和层叠绵延的群山,夏季风送来远方的清凉与草药芬芳。河水汤汤,白桦生长在山腰,黑魆魆的灌丛在山坡蔓延,路旁的高草下藏着草莓和蘑菇。林间寂静又喧响。松鸦机警,野兔蹦跳,赤狐躲在山冈。如果从荨麻旁经过,得小心翼翼,若稍不留神,荨麻的刺会刺得手指头又疼又痒……仿佛在此处,又似在别处,仿佛是现实,又似在文字的原野里纵横驰骋。
有时候,也会将书中事物与身边事物一一比对。大部分是植物,荨麻、大麻、苦艾、侧金盏花、燕子花,偶尔也有云雀鹞鹰之类。大致都能对得上。譬如荨麻,我们对它的称呼与书里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譬如苦艾,我们称其为苦蒿。也有一些植物,私下认定是它,却无法确认,譬如牛蒡。牛蒡在道路旁胡乱生长,大叶子如象耳招摇,开花,结出小刺猬似的果,人们将其随意称呼。我凭借文字描述和想象,猜测它就是俄罗斯原野上的牛蒡。以至于执拗多年,很多年后,终于得以确定。
那诸般贫瘠的年代,那种偶然获得的阅读是独特的,凄楚,却又瑰丽,迷人。那些文字灵动、活跃,生机勃勃,如野草披拂的小道,逐渐将我同一个遥远的世界相连。我得以走出,并进入一种广漠无际,在那里摸索、兜转,像我在生活中那样,行走山野,采撷种子与植物根茎。我将寻觅所得打包,扛起,返回我在山村的现实,植下它们。没有排异,没有抵触,两个世界竟然彼此补充,我因此很快熟识眼前草木,并得以知晓,在遥远寒凉的北方,它们同样生生不息。
读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随笔集《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其中一段文字忍不住多读了几遍:在被风吹得树干弯曲的白桦树后面,依稀可见远方的群山,层峦叠嶂,一片瓦蓝,交相辉映的天空同样瓦蓝、宽阔,一望无际的河口湾也泛出淡蓝色,浅沙滩上的草开始变黄。在高坡上曾坐落过村庄,有一些房屋还留下火炉、烟筒,拱形木板屋顶,房屋已经下沉。花楸树和稠李树表明这里曾是栅栏围着的房前小花园。村庄淹没在高高的杂草丛中,有一条勉强看得出的小道可以通行……不仅仅是因为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有似曾相识的风物,群山,溪流,灌木丛,白桦树,蓝天下是高坡上的村庄,炊烟寂静,如果是雨后,白云出岫……这段文字惹人回忆的,更多是童年时期的一种阅读体验。那时在祁连山东段一个三面环山的小村庄度过。交通闭塞,信息阻隔,八十年代初的人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有人外出读书,我是村中上学的为数不多的女孩之一。正是求知如渴的年龄,然而除去教材,除去几本辗转不已的连环画本,再无足够书籍可供阅读。记得一个日光漫漫的暑假,我从幽暗屋角扒出父亲曾经的课本,吹去浮尘,整理干净,有空时就坐在檐下石阶上一页页看。课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忘记,依稀记得有鲁迅的《风波》,附一幅黑白插图:河流、小船、长辫子的男人。或许有另一幅图,九斤老太捏着破芭蕉扇敲着桌凳。一字一字读,却只读得懂一个简单故事。至于江南水乡的风情,以及乌桕树、蒸干菜、独木桥,因为陌生,没激起多少兴趣。也翻出一本残破的描写俄罗斯原野的书籍(现在想来,该是《猎人笔记》或者《林中水滴》之类)读。发黄起皱有烟熏味和尘土味的纸页里,一个辽阔世界逐渐打开。那里季节分明,景物各异。如果是春天,大麻和荨麻发出馨香,矢车菊与铃兰同时开放;夏天,葱茏的黑麦和燕麦泛起涟漪,云雀在田地上空高高低低地叫,灌丛里到处是草莓和蘑菇,高大榛树黑黝黝矗立,树底下是松鼠和雪兔;到了九月,那里的白桦树通身金黄,寒鸦飞来飞去,雾凇在谷底闪耀白光,树丛深处,磨房轧轧地响……那世界那般熟悉又那般陌生,那般遥远又那般逼近。很快迷恋起来。一次不会读得太多,薄薄一本书,不能饕餮,得省着读,以打发漫长假日,有时是因为琐碎的家务活等我去做。某个午后,放下书本,拿起镰刀去山上割草。一步步在山路上走,遍野的迷蒙日光仿佛魔法,它将眼前世界与文字里的俄罗斯原野相重叠:宽广无际的蓝天和层叠绵延的群山,夏季风送来远方的清凉与草药芬芳。河水汤汤,白桦生长在山腰,黑魆魆的灌丛在山坡蔓延,路旁的高草下藏着草莓和蘑菇。林间寂静又喧响。松鸦机警,野兔蹦跳,赤狐躲在山冈。如果从荨麻旁经过,得小心翼翼,若稍不留神,荨麻的刺会刺得手指头又疼又痒……仿佛在此处,又似在别处,仿佛是现实,又似在文字的原野里纵横驰骋。有时候,也会将书中事物与身边事物一一比对。大部分是植物,荨麻、大麻、苦艾、侧金盏花、燕子花,偶尔也有云雀鹞鹰之类。大致都能对得上。譬如荨麻,我们对它的称呼与书里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譬如苦艾,我们称其为苦蒿。也有一些植物,私下认定是它,却无法确认,譬如牛蒡。牛蒡在道路旁胡乱生长,大叶子如象耳招摇,开花,结出小刺猬似的果,人们将其随意称呼。我凭借文字描述和想象,猜测它就是俄罗斯原野上的牛蒡。以至于执拗多年,很多年后,终于得以确定。那诸般贫瘠的年代,那种偶然获得的阅读是独特的,凄楚,却又瑰丽,迷人。那些文字灵动、活跃,生机勃勃,如野草披拂的小道,逐渐将我同一个遥远的世界相连。我得以走出,并进入一种广漠无际,在那里摸索、兜转,像我在生活中那样,行走山野,采撷种子与植物根茎。我将寻觅所得打包,扛起,返回我在山村的现实,植下它们。没有排异,没有抵触,两个世界竟然彼此补充,我因此很快熟识眼前草木,并得以知晓,在遥远寒凉的北方,它们同样生生不息。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