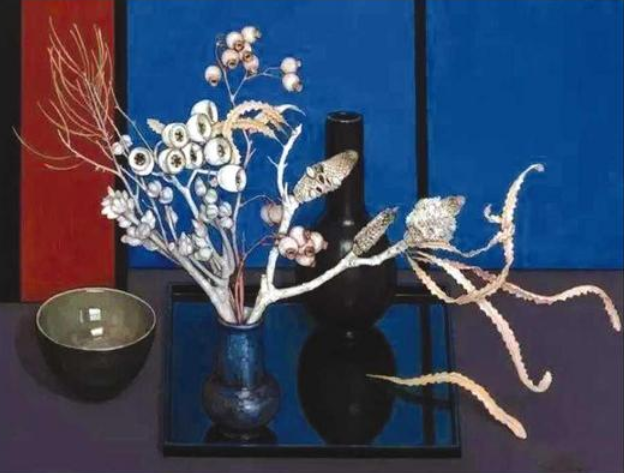魏振强的《村庄令》一书,是一片充满忧伤的乡村叙事场,一个个场景设置在乡村一隅:田野村舍,人与鸡豚牛羊,青山横于村外,溪水流向远方,画面清明。人向土地要生活,重复简单,无繁富奢华;互助友爱,无波澜玄机。故事早先沉淀于一位少年心底,待作家人到中年,仍以少时的视野去反观过往的世界,翻检过往的记忆,文字,单纯,和粹,率真,人物描写传神,与中国古典文学文法颇相契合。
《村庄令》叙事场景窄小,人物卑微,不外乎如费孝通先生早年所述“差序格局”中,“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之间的人际交往。所谓生活,无非辛酸。但作者却能以宁淡的心绪,去诉说少时沉重的“苦难”。尤其可贵的是人物叙写,笔法承接中国古文家的书写传统——小人物,见大情怀。
中国文学善写“小人物”的佳篇,左国迁班之文,随处可摭;宋以下文,屡见不鲜,欧阳修《泷冈阡表》、归有光《寒花葬志》、方苞《兄百川墓志》等名篇,皆以写小人物见长,其文法亦如中国传统诗论所谓“情动于中”“温柔敦厚”。即使像当代作家刘亮程散文名著《一个人的村庄》,也随处可见其对“小人物”用传统笔法的章节。《村庄令》以外婆鞠育提携之恩为主线,多场景描述外婆勤劳之苦,其中一节最为感人:“一天中午,我在家等外婆吃饭,等到别人快上工,也没见她回来。我就跑到那块地里。太阳太毒了,我光脚踩在土里,脚下像火一样烫。”接下来情景令人泪下:外婆瘦小的身躯弯曲着,她正在给山芋垄松土,胸前和背后印着大块大块白色的汗渍,我朝她打招呼,她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
这段描写与桐城古文家方苞回忆其少时与兄方舟道别时一段场面颇为相似:兄长余二岁。儿时,家无仆婢,五六岁即依兄卧起。兄赴芜湖之岁,将行,伏余背而流涕。
手足之情,流露于片言只语之间,令人一叹三嗟。
物质匮乏的年代,生产方式简单原始,一代代人甘于劳作,从生活中学会忍受,从大自然中承受一桩桩苦难。《村庄令》叙述的是过往的乡村记忆,其中涵泳了草木人生的文化意义。
“苦难”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必然承受的生存过程,那些年代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必讳言。一个民族若忘记甚至掩饰以往的苦难,幸福的明天就会失去其民族文化之根。《村庄令》带给我们的是一种 “苦难”生活的回味,书中一个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虽然尝尽酸甜苦辣,但负重而旷达,每一篇叙写都有沉郁的美学价值。例如《村庄令》“砸杏”一节:那户人家的半白瞎老太听到响声,追了过来,菊英就待在树上不动弹,我藏在一棵杂树后面,大气不敢出,不一会儿,老太太见没什么动静,骂骂咧咧地走了,菊英一哧溜下了树。
青涩顽劣的孩童,吝啬可怜的老人,对一棵果树的觎觑与护卫的情景,写得生动有趣,苦涩中透出快乐。
汪曾祺曾说:“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这句话的文外之味,即酸涩中带有一种去不掉的久远怀想。从农耕文化中走出来的人,无论贵贱,当他步入中年或进入老年以后,是守望家园,或是寄游四海,故乡的记忆都会背负在身上,作人生后半辈的心灵旅行。
许倬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中以独特的视角,从中国大众生活中的“小传统”进入,以 “安身立命,处事做人”建立起“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精神,论者称之为“生活肌肤中的中国文化”。《村庄令》中的“外婆”,是中国特定时代千万个生养我们的母性人物代表,她们与男子一同下地,在贫瘠的土地上,以简单的生产方式劳其筋骨,供养子孙,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以助人忍让为人生常理,甚至于巫、吊、祭祀之中来敬天悯人。她们身上所具备善良、坚忍的优秀品格,曾经陶冶了一代代人的性格,也必将为子孙后代提供人生范本。
卑微的人生不乏善良与坚忍,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品德。四千年农夫生活无非草木人间,《村庄令》所呈现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
【橙美文】书写的意义
安徽商报
张雪子
2023-07-03 09:44:55
魏振强的《村庄令》一书,是一片充满忧伤的乡村叙事场,一个个场景设置在乡村一隅:田野村舍,人与鸡豚牛羊,青山横于村外,溪水流向远方,画面清明。人向土地要生活,重复简单,无繁富奢华;互助友爱,无波澜玄机。故事早先沉淀于一位少年心底,待作家人到中年,仍以少时的视野去反观过往的世界,翻检过往的记忆,文字,单纯,和粹,率真,人物描写传神,与中国古典文学文法颇相契合。
《村庄令》叙事场景窄小,人物卑微,不外乎如费孝通先生早年所述“差序格局”中,“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之间的人际交往。所谓生活,无非辛酸。但作者却能以宁淡的心绪,去诉说少时沉重的“苦难”。尤其可贵的是人物叙写,笔法承接中国古文家的书写传统——小人物,见大情怀。
中国文学善写“小人物”的佳篇,左国迁班之文,随处可摭;宋以下文,屡见不鲜,欧阳修《泷冈阡表》、归有光《寒花葬志》、方苞《兄百川墓志》等名篇,皆以写小人物见长,其文法亦如中国传统诗论所谓“情动于中”“温柔敦厚”。即使像当代作家刘亮程散文名著《一个人的村庄》,也随处可见其对“小人物”用传统笔法的章节。《村庄令》以外婆鞠育提携之恩为主线,多场景描述外婆勤劳之苦,其中一节最为感人:“一天中午,我在家等外婆吃饭,等到别人快上工,也没见她回来。我就跑到那块地里。太阳太毒了,我光脚踩在土里,脚下像火一样烫。”接下来情景令人泪下:外婆瘦小的身躯弯曲着,她正在给山芋垄松土,胸前和背后印着大块大块白色的汗渍,我朝她打招呼,她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
这段描写与桐城古文家方苞回忆其少时与兄方舟道别时一段场面颇为相似:兄长余二岁。儿时,家无仆婢,五六岁即依兄卧起。兄赴芜湖之岁,将行,伏余背而流涕。
手足之情,流露于片言只语之间,令人一叹三嗟。
物质匮乏的年代,生产方式简单原始,一代代人甘于劳作,从生活中学会忍受,从大自然中承受一桩桩苦难。《村庄令》叙述的是过往的乡村记忆,其中涵泳了草木人生的文化意义。
“苦难”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必然承受的生存过程,那些年代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必讳言。一个民族若忘记甚至掩饰以往的苦难,幸福的明天就会失去其民族文化之根。《村庄令》带给我们的是一种 “苦难”生活的回味,书中一个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虽然尝尽酸甜苦辣,但负重而旷达,每一篇叙写都有沉郁的美学价值。例如《村庄令》“砸杏”一节:那户人家的半白瞎老太听到响声,追了过来,菊英就待在树上不动弹,我藏在一棵杂树后面,大气不敢出,不一会儿,老太太见没什么动静,骂骂咧咧地走了,菊英一哧溜下了树。
青涩顽劣的孩童,吝啬可怜的老人,对一棵果树的觎觑与护卫的情景,写得生动有趣,苦涩中透出快乐。
汪曾祺曾说:“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这句话的文外之味,即酸涩中带有一种去不掉的久远怀想。从农耕文化中走出来的人,无论贵贱,当他步入中年或进入老年以后,是守望家园,或是寄游四海,故乡的记忆都会背负在身上,作人生后半辈的心灵旅行。
许倬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中以独特的视角,从中国大众生活中的“小传统”进入,以 “安身立命,处事做人”建立起“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精神,论者称之为“生活肌肤中的中国文化”。《村庄令》中的“外婆”,是中国特定时代千万个生养我们的母性人物代表,她们与男子一同下地,在贫瘠的土地上,以简单的生产方式劳其筋骨,供养子孙,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以助人忍让为人生常理,甚至于巫、吊、祭祀之中来敬天悯人。她们身上所具备善良、坚忍的优秀品格,曾经陶冶了一代代人的性格,也必将为子孙后代提供人生范本。
卑微的人生不乏善良与坚忍,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品德。四千年农夫生活无非草木人间,《村庄令》所呈现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
魏振强的《村庄令》一书,是一片充满忧伤的乡村叙事场,一个个场景设置在乡村一隅:田野村舍,人与鸡豚牛羊,青山横于村外,溪水流向远方,画面清明。人向土地要生活,重复简单,无繁富奢华;互助友爱,无波澜玄机。故事早先沉淀于一位少年心底,待作家人到中年,仍以少时的视野去反观过往的世界,翻检过往的记忆,文字,单纯,和粹,率真,人物描写传神,与中国古典文学文法颇相契合。《村庄令》叙事场景窄小,人物卑微,不外乎如费孝通先生早年所述“差序格局”中,“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之间的人际交往。所谓生活,无非辛酸。但作者却能以宁淡的心绪,去诉说少时沉重的“苦难”。尤其可贵的是人物叙写,笔法承接中国古文家的书写传统——小人物,见大情怀。中国文学善写“小人物”的佳篇,左国迁班之文,随处可摭;宋以下文,屡见不鲜,欧阳修《泷冈阡表》、归有光《寒花葬志》、方苞《兄百川墓志》等名篇,皆以写小人物见长,其文法亦如中国传统诗论所谓“情动于中”“温柔敦厚”。即使像当代作家刘亮程散文名著《一个人的村庄》,也随处可见其对“小人物”用传统笔法的章节。《村庄令》以外婆鞠育提携之恩为主线,多场景描述外婆勤劳之苦,其中一节最为感人:“一天中午,我在家等外婆吃饭,等到别人快上工,也没见她回来。我就跑到那块地里。太阳太毒了,我光脚踩在土里,脚下像火一样烫。”接下来情景令人泪下:外婆瘦小的身躯弯曲着,她正在给山芋垄松土,胸前和背后印着大块大块白色的汗渍,我朝她打招呼,她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这段描写与桐城古文家方苞回忆其少时与兄方舟道别时一段场面颇为相似:兄长余二岁。儿时,家无仆婢,五六岁即依兄卧起。兄赴芜湖之岁,将行,伏余背而流涕。手足之情,流露于片言只语之间,令人一叹三嗟。物质匮乏的年代,生产方式简单原始,一代代人甘于劳作,从生活中学会忍受,从大自然中承受一桩桩苦难。《村庄令》叙述的是过往的乡村记忆,其中涵泳了草木人生的文化意义。“苦难”是人类社会进步中必然承受的生存过程,那些年代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必讳言。一个民族若忘记甚至掩饰以往的苦难,幸福的明天就会失去其民族文化之根。《村庄令》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苦难”生活的回味,书中一个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虽然尝尽酸甜苦辣,但负重而旷达,每一篇叙写都有沉郁的美学价值。例如《村庄令》“砸杏”一节:那户人家的半白瞎老太听到响声,追了过来,菊英就待在树上不动弹,我藏在一棵杂树后面,大气不敢出,不一会儿,老太太见没什么动静,骂骂咧咧地走了,菊英一哧溜下了树。青涩顽劣的孩童,吝啬可怜的老人,对一棵果树的觎觑与护卫的情景,写得生动有趣,苦涩中透出快乐。汪曾祺曾说:“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这句话的文外之味,即酸涩中带有一种去不掉的久远怀想。从农耕文化中走出来的人,无论贵贱,当他步入中年或进入老年以后,是守望家园,或是寄游四海,故乡的记忆都会背负在身上,作人生后半辈的心灵旅行。许倬云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一书中以独特的视角,从中国大众生活中的“小传统”进入,以“安身立命,处事做人”建立起“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中国文化”精神,论者称之为“生活肌肤中的中国文化”。《村庄令》中的“外婆”,是中国特定时代千万个生养我们的母性人物代表,她们与男子一同下地,在贫瘠的土地上,以简单的生产方式劳其筋骨,供养子孙,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以助人忍让为人生常理,甚至于巫、吊、祭祀之中来敬天悯人。她们身上所具备善良、坚忍的优秀品格,曾经陶冶了一代代人的性格,也必将为子孙后代提供人生范本。卑微的人生不乏善良与坚忍,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品德。四千年农夫生活无非草木人间,《村庄令》所呈现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