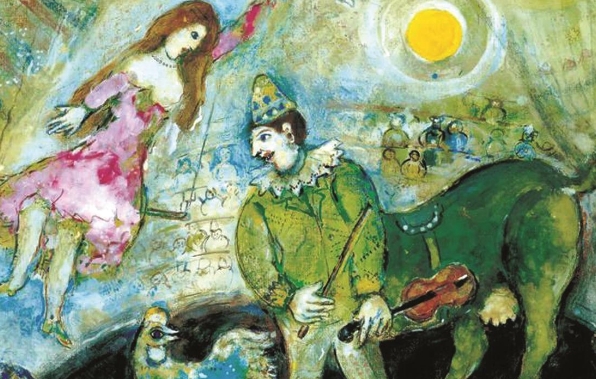简笔画一般,两朵硕大的蔷薇花团团抱紧,像漩涡儿,层层递进。直挺挺的花枝上,衬以金铂色的六枚叶片。花根的近左,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零星碎片,具有某种寓意吗?这是《金蔷薇》的封面。它一直在我心里……
静17岁时,我16岁。我们一并坐进了化工技校的同一班级。她是工厂子弟,我是外面考进来的,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打成一片”。但静的确不与人同,她终日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不仅不跟男生说话,跟女生也不说,仿佛是整个群体的局外人,直到我们同时爱上写作——那时,“写作”是多么隆重的“事件”啊,尤其对于两个半大的孩子来说。
当时,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处在从他市拨离出来的交替时期。报纸试刊时,我便在报“屁股”之类不显眼的地方刊发了几篇诗、文,皆为豆腐块般的浅淡抒怀——不浅淡,还能是什么呢?转年,市报创刊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于福音。之于我,更是写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盘锦日报》创刊号的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小说,而且是——头条。这幸福太巨大了!我觉得,第一时间与静分享才有意义。
怀揣着烈焰,我欣欣然前往“报喜”。而静却像她的名字一样,冷冷地泼过来一盆“凉水”:“那算什么呀!我早就发表过了。”
静的爸爸在单位身居要职,她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极尽亲人的宠爱。加之,本厂子弟的优越性,如无空不入的细菌——不过,它发酵,却也成就了有益的一面。不知是“外来者”介入“本土”的急切心理,还是静独特的气息,自尊心极强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向她趋近。
夏日午饭后漫长的时光,我总会骑上自行车去她家,到她的小屋呆一呆。静的小屋很小,容我们两人便无法转身。小屋墙壁上,没有贴着风行一时的张曼玉、钟楚红等港台明星大头像,吸引我的却是靠墙角站立着的小书架。那时,我们正狂热地追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那天,静从小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几天我又读了一遍。可是,每次我都觉得苏珊娜不是同一个人了,奇怪不。”
我捧起书。“《金蔷薇》”,我读出声来,作者名字太长了!她看我一脸茫然,冷冷地说:“这本书你都不知道,还搞什么创作?!”
后来,我们毕业了。我被分到全厂最好的中心化验室,成为水质化验员,静却被分到最脏最累的一线生产车间。她更孤僻了。再后来,她去了报社做编辑。而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她却一点动静没有,并时不时对我们的种种世俗行为嗤之以鼻。可是,当我们都认为她一定是个不婚族,她却结婚生子了。
我去她的公寓看望她和孩子。她一改从前,完全变得与我们一样婆婆妈妈。我真心替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女孩该有的“温度”。我说我的农历生日恰好与他儿子的阳历生日相同。她开心地说,那就借你的吉祥喽。说话时,满脸笑意和真诚。
在她家,我又看到了那本《金蔷薇》,我又想起了初读时的惊喜与眼泪。可我并没说。因为我已真切地看到,文学的味道像那朵金蔷薇和苏珊娜的蓝色发带一般幽香——那幽香,已散在她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了。我终于放心了。
再次收到她的消息,是得知她去了国外之后。再后来,又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不断地听到她的种种际遇,替她担心,又不敢问候,直至听到她患病去世的消息……唉!那么年轻!至今,我仍在恍惚中,无法释怀……岁月恒常,却阴阳永隔。我时常想起,我们互相传看对方硬皮塑料笔记本上抄写的美丽诗文;时常想起,我们在课间时互递一个会意的眼神儿,就会在学校断墙外的荒草滩上聚拢,分享彼此又发表的新作——那正是我如今依旧“点灯熬油”深爱文字的理由。我们都是尘土,珍贵亦或使大地更加深沉,已经足够。我记住的永远是她30岁之前的面容。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本是约等于无的微尘。但我相信,有些“尘土”是异常珍贵的,无影、无形甚至“微毒”,却足以把你营养、治愈……
(飒飒)
【橙美文】往昔珍贵的尘土
安徽商报
张雪子
2024-01-08 10:04:42
简笔画一般,两朵硕大的蔷薇花团团抱紧,像漩涡儿,层层递进。直挺挺的花枝上,衬以金铂色的六枚叶片。花根的近左,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零星碎片,具有某种寓意吗?这是《金蔷薇》的封面。它一直在我心里……
静17岁时,我16岁。我们一并坐进了化工技校的同一班级。她是工厂子弟,我是外面考进来的,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打成一片”。但静的确不与人同,她终日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不仅不跟男生说话,跟女生也不说,仿佛是整个群体的局外人,直到我们同时爱上写作——那时,“写作”是多么隆重的“事件”啊,尤其对于两个半大的孩子来说。
当时,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处在从他市拨离出来的交替时期。报纸试刊时,我便在报“屁股”之类不显眼的地方刊发了几篇诗、文,皆为豆腐块般的浅淡抒怀——不浅淡,还能是什么呢?转年,市报创刊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于福音。之于我,更是写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盘锦日报》创刊号的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小说,而且是——头条。这幸福太巨大了!我觉得,第一时间与静分享才有意义。
怀揣着烈焰,我欣欣然前往“报喜”。而静却像她的名字一样,冷冷地泼过来一盆“凉水”:“那算什么呀!我早就发表过了。”
静的爸爸在单位身居要职,她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极尽亲人的宠爱。加之,本厂子弟的优越性,如无空不入的细菌——不过,它发酵,却也成就了有益的一面。不知是“外来者”介入“本土”的急切心理,还是静独特的气息,自尊心极强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向她趋近。
夏日午饭后漫长的时光,我总会骑上自行车去她家,到她的小屋呆一呆。静的小屋很小,容我们两人便无法转身。小屋墙壁上,没有贴着风行一时的张曼玉、钟楚红等港台明星大头像,吸引我的却是靠墙角站立着的小书架。那时,我们正狂热地追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那天,静从小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几天我又读了一遍。可是,每次我都觉得苏珊娜不是同一个人了,奇怪不。”
我捧起书。“《金蔷薇》”,我读出声来,作者名字太长了!她看我一脸茫然,冷冷地说:“这本书你都不知道,还搞什么创作?!”
后来,我们毕业了。我被分到全厂最好的中心化验室,成为水质化验员,静却被分到最脏最累的一线生产车间。她更孤僻了。再后来,她去了报社做编辑。而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她却一点动静没有,并时不时对我们的种种世俗行为嗤之以鼻。可是,当我们都认为她一定是个不婚族,她却结婚生子了。
我去她的公寓看望她和孩子。她一改从前,完全变得与我们一样婆婆妈妈。我真心替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女孩该有的“温度”。我说我的农历生日恰好与他儿子的阳历生日相同。她开心地说,那就借你的吉祥喽。说话时,满脸笑意和真诚。
在她家,我又看到了那本《金蔷薇》,我又想起了初读时的惊喜与眼泪。可我并没说。因为我已真切地看到,文学的味道像那朵金蔷薇和苏珊娜的蓝色发带一般幽香——那幽香,已散在她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了。我终于放心了。
再次收到她的消息,是得知她去了国外之后。再后来,又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不断地听到她的种种际遇,替她担心,又不敢问候,直至听到她患病去世的消息……唉!那么年轻!至今,我仍在恍惚中,无法释怀……岁月恒常,却阴阳永隔。我时常想起,我们互相传看对方硬皮塑料笔记本上抄写的美丽诗文;时常想起,我们在课间时互递一个会意的眼神儿,就会在学校断墙外的荒草滩上聚拢,分享彼此又发表的新作——那正是我如今依旧“点灯熬油”深爱文字的理由。我们都是尘土,珍贵亦或使大地更加深沉,已经足够。我记住的永远是她30岁之前的面容。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本是约等于无的微尘。但我相信,有些“尘土”是异常珍贵的,无影、无形甚至“微毒”,却足以把你营养、治愈……
(飒飒)
简笔画一般,两朵硕大的蔷薇花团团抱紧,像漩涡儿,层层递进。直挺挺的花枝上,衬以金铂色的六枚叶片。花根的近左,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零星碎片,具有某种寓意吗?这是《金蔷薇》的封面。它一直在我心里……静17岁时,我16岁。我们一并坐进了化工技校的同一班级。她是工厂子弟,我是外面考进来的,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打成一片”。但静的确不与人同,她终日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不仅不跟男生说话,跟女生也不说,仿佛是整个群体的局外人,直到我们同时爱上写作——那时,“写作”是多么隆重的“事件”啊,尤其对于两个半大的孩子来说。当时,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处在从他市拨离出来的交替时期。报纸试刊时,我便在报“屁股”之类不显眼的地方刊发了几篇诗、文,皆为豆腐块般的浅淡抒怀——不浅淡,还能是什么呢?转年,市报创刊了。对于写作者来说,不啻于福音。之于我,更是写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盘锦日报》创刊号的副刊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小说,而且是——头条。这幸福太巨大了!我觉得,第一时间与静分享才有意义。怀揣着烈焰,我欣欣然前往“报喜”。而静却像她的名字一样,冷冷地泼过来一盆“凉水”:“那算什么呀!我早就发表过了。”静的爸爸在单位身居要职,她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极尽亲人的宠爱。加之,本厂子弟的优越性,如无空不入的细菌——不过,它发酵,却也成就了有益的一面。不知是“外来者”介入“本土”的急切心理,还是静独特的气息,自尊心极强的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向她趋近。夏日午饭后漫长的时光,我总会骑上自行车去她家,到她的小屋呆一呆。静的小屋很小,容我们两人便无法转身。小屋墙壁上,没有贴着风行一时的张曼玉、钟楚红等港台明星大头像,吸引我的却是靠墙角站立着的小书架。那时,我们正狂热地追俄罗斯文学、拉美文学。那天,静从小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几天我又读了一遍。可是,每次我都觉得苏珊娜不是同一个人了,奇怪不。”我捧起书。“《金蔷薇》”,我读出声来,作者名字太长了!她看我一脸茫然,冷冷地说:“这本书你都不知道,还搞什么创作?!”后来,我们毕业了。我被分到全厂最好的中心化验室,成为水质化验员,静却被分到最脏最累的一线生产车间。她更孤僻了。再后来,她去了报社做编辑。而我,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结婚、生子。她却一点动静没有,并时不时对我们的种种世俗行为嗤之以鼻。可是,当我们都认为她一定是个不婚族,她却结婚生子了。我去她的公寓看望她和孩子。她一改从前,完全变得与我们一样婆婆妈妈。我真心替她高兴,她终于有了女孩该有的“温度”。我说我的农历生日恰好与他儿子的阳历生日相同。她开心地说,那就借你的吉祥喽。说话时,满脸笑意和真诚。在她家,我又看到了那本《金蔷薇》,我又想起了初读时的惊喜与眼泪。可我并没说。因为我已真切地看到,文学的味道像那朵金蔷薇和苏珊娜的蓝色发带一般幽香——那幽香,已散在她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了。我终于放心了。再次收到她的消息,是得知她去了国外之后。再后来,又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不断地听到她的种种际遇,替她担心,又不敢问候,直至听到她患病去世的消息……唉!那么年轻!至今,我仍在恍惚中,无法释怀……岁月恒常,却阴阳永隔。我时常想起,我们互相传看对方硬皮塑料笔记本上抄写的美丽诗文;时常想起,我们在课间时互递一个会意的眼神儿,就会在学校断墙外的荒草滩上聚拢,分享彼此又发表的新作——那正是我如今依旧“点灯熬油”深爱文字的理由。我们都是尘土,珍贵亦或使大地更加深沉,已经足够。我记住的永远是她30岁之前的面容。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本是约等于无的微尘。但我相信,有些“尘土”是异常珍贵的,无影、无形甚至“微毒”,却足以把你营养、治愈……(飒飒)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