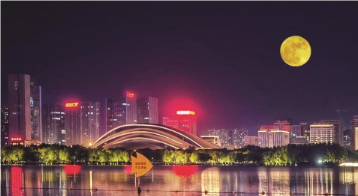回到了乡下老家。母亲问我吃什么饭。我随口说,吃麻食吧。母亲随手摘下房檐下一顶旧草帽,就张罗着做饭去了。草帽作为日常的雨具,在家乡可是一种制作麻食的工具,为的是搓上草帽缏上的花纹,沾上草木的清香。
麻食是家乡关中地区的面食,形状如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面疙瘩,是家乡特有的小吃。
和面,醒面,掐指蛋大面团在洗净的草帽沿上搓。搓麻食,是个技术活。全靠指尖上的功夫,麻食形似猫耳朵,周身花纹,宛如一个个螺丝卷,小巧玲珑,十分美观。入锅后久煮不烂,光滑筋韧,佐以鲜肉臊子,丁丁菜,其味鲜香隽永。
无论是一锅烩,还是浇上油泼辣子热拌,都令人回味无穷。麻食口味筋道,汤料味道浓郁,汤中配上时令蔬菜,可做出百变花样。乡下人家,家家厨房里,都有一套独特的秘方。虽说万变不离其宗,它总归是麻食,但可以尽着自己的性情变汤变菜。
尤其在寒冷的冬天,下雨天,全家齐上阵,煮一锅煎火的麻食,让人浑身舒畅,寒意荡然无存。
小时候,母亲每次搓麻食,都令我兴奋不已,主要是搓麻食的乐趣。母亲忙活着和面,我在一边洗草帽。一顶草帽边沿上,几双手在忙活,一搓一卷,叽叽喳喳,不亦乐乎,快乐的笑声一直荡漾在记忆深处。
在乡间,还有一种懒麻食。农人下地归来,又困又累,为节省时间,农妇总会和一团面,擀开,切成小正方形,以手反复揉搓卷成田螺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农村小学任教。夏收假,我给毕业班学生补课,吃饭成了问题。山里孩子憨厚老实,而且爱老师。到了吃饭时间,孩子们一拥而上挤进厨房给我搓麻食。逼仄灶房里,一群孩子像一只只小燕子,忙忙碌碌。摘菜的,生火的,和面的,烧水的,不一会儿,大功告成,我们师生分享着劳动成果,格外高兴。那天的烩麻食,是我吃的最美味的一次,更加坚定了当老师的信心。那十多天,和孩子们天天搓麻食,配以木耳,其味独特,地道。后来,我调离了那所农村小学,但是那里的烩麻食,终身难忘……
说话间,母亲的手工麻食已经上了桌,味道还是那么地道。
(曹雪柏)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