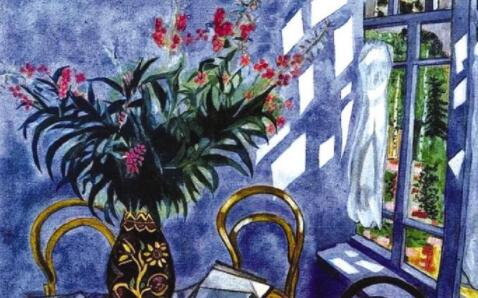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李商隐这句诗,之前看过所有版本释义,直觉都是错误的。但,我自己也想不太明白……
有一天夜里,看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第六集《相见难》讲李商隐。其中,王屋山寻觅李之遗踪的一个镜头,简直电光石火,一下明白过来。是一个仰拍镜头,摄像机慢慢自林间一摇到底——钴蓝天上繁星闪烁,可不就是“星沉海底”么?原是一个暗喻。山中没有光污染,人坐窗前,漫天星斗毕现眼前,钴蓝的天大海一样,星星宛如沉到海底……如若神启,激动得久不能睡。
李商隐的诗是真好,一直在确定不确定之间,克制,简洁,深情,反复回旋,意象纷呈,无尽的歧义……但内核,永远在那里闪闪发光。
二
许多时候,文字是活出来的,并非写出来的。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夜雨寄北》,也是别样的好。“君”,远方的人,心心相印的人。大约来了一封信,诉尽思念,末了问一声:你几时回长安?
李商隐将情感的复杂、矛盾,表达得九曲回肠。
“未有期”,人生里大多时刻,我们是作不了主的,也是无奈语。君问归期未有期,就是说,并非我不曾思念你,最终还得由命运安排。
当时的他在巴蜀一幕府中,做着一份秘书的工,还得看上司脸色,又无年休假。就算有,那几天假,也不够走到长安的。
山河阻隔。古时,无非坐船,抑或骑马,来回一趟,短则数月,长则半年。见一面真难,真是天涯途远,唯余相互思念,炽热又绝望。
李白半生于行旅之中,多是沿着长江走,于皖南盘桓多年,主要是缺乏快捷的交通工具。
时间日月都走得慢。什么都是慢的,一颗心自有清静。静则生慧,去浮躁,得专注,故能一点点把绘画书法搞到艺术的高度,产出无数魏碑啊,菩萨石像啊……数年不渝。每个人都有一颗艺术心。现在交通发达,一日千里,人人处在疯狂状态里,连小城正定隆兴寺里那尊观音佛像,即便被后人粉刷一下,都搞得那么伧俗,他就不能静下心来查查资料,寻觅寻觅一些特殊的矿物颜料,好好地修旧如旧一番。
再回到这首诗。我们对于未来的期待,十之八九要落空。从现在时写到未来时,再转到当下——巴山夜雨涨秋池。此刻,我这里正下着大雨。秋风秋雨,落叶满地,心情湿漉而滞重。忽然语气一转,“何当共剪西窗烛”,这是心未死,便有憧憬——我们何时有秉烛夜谈的那一刻呢。“共剪西窗烛”这一意象,无比诗性。最末一句,“却话巴山夜雨时”,颇为诡异。看怎么理解了。也可以是,到时见面了,要好好说说我在蜀地的雨夜。雨夜有什么追忆的呢?不,是雨夜对你殷切的思念……“却话”,这确定不确定的语气,最是含蓄深情,牵动肝肠。
有人非说是写给妻子的。鬼扯瓢!写给妻子的诗,岂有如此辗转?对妻,如对亲人。如此黏稠浓得化不开的深情,永无可能,更不合人性。
他是谁?李商隐啊,一个情感极度丰沛的人。
想必写给知己的。半生颠沛流离,到处打工,冲天的才华全部用来写诗了。蜀地,他呆过,北越之地桂林也去过……欣赏他提携他的人突然离世,无奈的他,重回长安,妻子已逝。
也不知那位知己可还在。
三
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一次次破碎中不改真挚的人。
一直偏爱这句诗,不曾去翻过卷轶浩繁的释义。所有解释,都是俗气平庸的。人们何曾懂得过诗人的灵魂景深?
随着年岁叠加,我自有我的理解。无非:于我言,你是世间唯一宝珠,愿将你封存于水晶盒中,如晤如对,一生不变。除此,世界与我无涉。不论你意于我何,只愿同沐一轮月,共饮一江水……
这个承诺太重了,搭上一生。但谁又能把握未来的心意呢?只是,此刻,我确乎奉上了我仅有的灵魂……
李商隐的诗域不仅宽广,更有纵深。我们对于他的理解,也是日渐地对于自己的理解。一部《诗经》,不同年龄段翻开,都是迥异人生滋味。如此,我们读书,并非单纯悟出来的,同样也是活出来的。境界到了,人便到了。
幼时,可曾懂得“心心相印”这个词?直至读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两颗心打破物理界限叠合于一起了么?并不,而是纵然远隔千山万水,彼此却也心意相通。李商隐确乎惊才绝绝,轻易写出两性之间的灵魂契合。
四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写了什么?还是思而不得。
曾在云南巍山的一个良夜,登拱辰楼,邂逅一架古瑟,也曾亲手触摸过。可惜前几年,一场大火,毁了拱辰楼内所有。古瑟已然不存,它并非五十弦,诗人夸张了,也许另有所指?
珠有泪,玉生烟。多美的意象。蚌病成珠,杜鹃啼血,不过都是拟人手法,珍珠为泪水所磨成。长安附近的蓝田,古时产玉吧,云岚缭绕成烟,天空何等透蓝……
一直想去终南山一带,沿着唐诗的气韵走,追寻韩愈、王维、李商隐之遗踪。可惜,未能成行。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当下延伸至未来时,再回到当下。实则,当下早已成为了过去。他依然两手空空。
生而为人,我们的一生均为不同的执念所纠缠。如今,再读这首诗,反而挣脱掉小我的情感束缚,而是将其视作整个人生的遭际摹写,不过是求而不得吧。你看我们的写作,何尝不是“晓梦迷蝴蝶”,又何以不是“春心托杜鹃”呢?不写,简直活不下去。
不论是一个具象的人,抑或抽象的文学,皆是值得我们追求并热爱终生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生命短暂,我们愿意化身所有,去爱着这个世间,哪怕一阵微风,一片落花。
每当深秋,秋雨淋漓,心间总是要浮起他那句惆怅之诗: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当年,屡屡科考不第的他,去到河南王屋山寻道,一路颓废迷茫。落叶人何在——他到底在追寻什么呢?当真是一名得道高僧么?实则,他找的莫非自己?是寻觅一个灵魂的归处。寒云太厚,遮蔽了艰难征途。偌大的山,也容不下他一个小小的人。
一生均在寻觅归途的他,到底写出了人类共同的宿命感。
故,每每谈及李商隐,总是让人叹气。叹息他的诗,如此幽深折曲,写尽一切不如意。以如此纷繁意象,铺陈生命真相,我们一生均在失去着……
但,一生失意的李商隐,却在诗歌中得到所有。他以一支传彩笔刻画着自己,成全着自己,终究成为繁星中一员,一直璀璨下去了。
(钱红丽)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