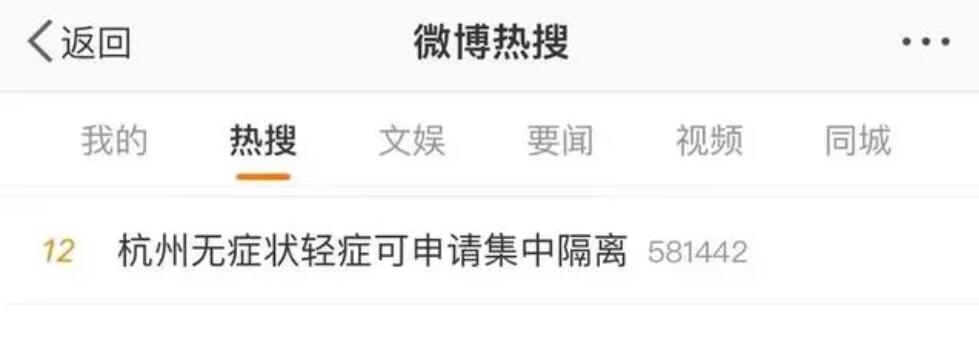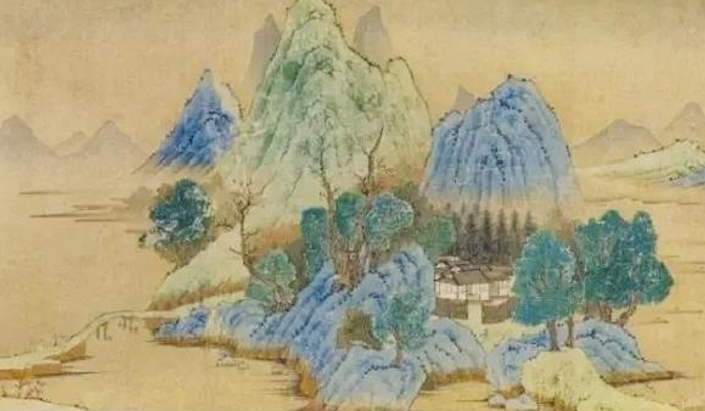生活在别处
◎杨菁菁
身体略好了一点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可以出去旅行了。
整个2022年,只出过三次省,几乎每次都在“惊险”的边缘游走。没什么是确定的,出门之后,每天都在不断查找新的防疫政策和接待政策,这让我,一个资深的旅人都颇觉得困难重重。后来小孩上学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整整四个月,我们哪儿都没去。
但今年,一切都好起来了。元旦那天凌晨,我在屏幕这头,看着步行街汹涌的人潮在新年钟声敲响时放飞了气球,竟然有些热泪盈眶。从来都不喜人多,但是有了人,才有希望不是么?
今年,应该终于可以实现那个攒了好几年的愿望,去山西看古建了。
偶然读到一则新闻,山西临汾一个村里,一位老太太病重不治。她和儿子说,把治疗费用省下来,去修好村里的一座楼——这座几百年的明代建筑早已残破不堪。老人仙逝后,子女筹资百万,加上政府拨资四十万元,村里的人同心共济,修复了这座即将倾颓的玉皇楼。据说山西民间,至今还有许多擅长砖木雕和漆画的传统匠人,民众自古以来就有自发维护古建的传统。“地上文物看山西”,除了存世量极大之外,从人们内心发出的这种对古建的维护感,才是古建富有长久生命力的真正原因吧。
今年打算飞去运城,租车去黄河边,看风陵渡、鹳雀楼,再一路北上,去看万荣飞云楼。这条线路,我在内心已经规划了不下十次。是先到三门峡,还是先到运城?许多古建的细节,我在图册上无数次揣摩过,只差亲身去看一看。要看就要趁早,大多数文保单位都是籍籍无名的,可能会因为某次大修就长达数年不开放,例如那年水灾后关闭的巩义石窟寺。与来自时间里的古物相聚,最重要的还是缘分。我曾震撼于应县木塔的精巧,去晚了,木塔早就不再让游客登临。也曾在假日赶到悬空寺,因游客过多,也无缘得以一观。但去过就够了,哪怕无法看清每一个木构,每一个斗拱,每一处壁画,能在远处遥遥致意,也算是一种与岁月的相逢。就像如今看敦煌壁画,网上有极为高清的资源,纤毫毕现,比亲眼去看还要明晰。但人们为什么还是要去到石窟寺?只为了站在那儿,感受下吹了一千年的风。傍晚了,夕阳遥遥从三危山的洞窟敛去,远处的砂砾在风的洗礼下,吹成条条缕缕的沙海,宕泉河的水流啊流。供养人、僧人、匠人、信众还有普通人,他们都曾打这儿路过,赞叹喜悦。我也来了,加入赞叹喜悦的行列。
这几年,步入中年,生活可用“乏味”来形容。“审美”成了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亮色。上下班途中遇到的花朵,某日特别蓝的天,博物馆里开了个新展,这些都能激起生命中的兴发感动。它提醒我时时感恩,因为活着,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生命体验。
又可以远行了,今年大概还要去一次南方的海边。比如飞到潮汕,在潮州古城好好逛一逛,看看牌楼,看看老厝;再租一辆车开到东山岛,在海边结庐而居,吹吹海风。我或许能捡到一百个美丽的贝壳。再或许我能和渔船一起出海,打到当天的第一网鱼,在夜晚燃起篝火,烤鱼并且喝酒。偶尔也需要一种迥异日常的生活方式,用空间打断一下日常,人为制造出某种“新的开始”。如果没有家乡,远行将失去意义。知道锚在何处,我们才能永远惦记着远方。
今年或者明年的雪季,我要带着孩子去一趟东北,看看大如席的雪花,看看结满冰的河流。我向他许愿,我们会在厚厚的冰面上坐着雪橇玩耍。会看到像城堡一样高耸入云的冰雕,以及有些冰雕可以从三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滑下。我们要穿得严严实实,像一只熊,在比冰箱还要冷的天地中撒欢打滚。运气好我们能遇到一场大雪,雪变成冰。然后再也不会融化。我们要北上,去纬度高的地方体验寒冷、体验霜冻、体验滴水成冰的快乐。北境是一个新世界,令人念念不忘。
我猜想,我们还会在一个东北味儿十足的小饭店,盘腿坐在炕上吃粉条炖大马哈鱼以及哈尔滨红肠,每一盘菜,都有我们家乡的两份那么多。吃饱之后,我们慢慢走回住处,也许还会在某个仓买的门口碰到露天摆放的雪糕。买一支,冲进暖融融的屋子,边吃,边看玻璃窗上的热气化作一条条水珠流下。我们在上面写字。北方啊,你好。
即使是对旅行的想象也让我心潮澎湃,我甚至还没来得及想那些更远的地方,例如米兰、惠灵顿、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小我就认为我是个旅人,后来我真的成了一个旅人。我生活在此处,也生活在别处。

旅行箱里的人生
◎陶妍妍
新年收到一件礼物,是插画家卤猫的绘本集《旅行箱里的四季》。
喜欢卤猫很久了,他爱一个人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画画——在春天老家的《橘园》里午睡,在夏天《摩洛哥的马约尔花园》里凝望睡莲,秋天去《下雨天的东京塔》下赴约,冬天的《冰湖》上,我与这个世界共同冷冽。
送我这本书的,是一个在上海独自打拼的姑娘。去年五月,在出租屋吃了一个月的冷冻玉米、胡萝卜和洋葱。每次给她打电话,都说,“老师我很好,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很忙,没空和你多说,你照顾好自己。”然后像一尾鱼,潜入深海,连水泡都寻不见。
年前,我在床上躺得昏天黑地,她快递来这本书及一大盆白色蝴蝶兰。我说什么年景,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她坚持说,要好好迎接新年啊,因为生活必须充满希望。
书的封面是一张名为《智利沙漠》的纸本水粉,远景是土黄色山丘,然后是绵延的桃红色花海,戴黑色礼帽的卤猫和他的狗狗,一起在画面中央,边走边唱。
我特地查了资料,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平均年降水量少雨0.1毫米,被称为世界“旱极”,旱到甚至找不出细菌。但就是这样一片土地,每5到7年,在9~11月南半球的春天里,休眠多年的龙爪球和智利球的种子,在一场暴风雨中,如同得到神的召唤,从皲裂的土地上蓬勃而出,用毕生力气,出演一次生命的狂欢。
这个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总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奇迹正发生。
前几天刷到周轶君一条短视频,她说:“世界观的匮乏,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不是地图上概念,而是你真的走过去,噢,这里是高原还是平原,这里的人这样生活,当你建立起它们的地理观念后,从某种意义上才可以平视它,不会再用一种或高或低的不准确的观念来看它,因为你知道,它所有的生活方式也好,价值观也好,都是由于它的地理人文所决定的。”
深以为然。
人生的很多烦恼,都来自揣测产生的忐忑;拥有越少的人,越容易坚持己见;见识,不应该简单等同于享受,更约等于接纳——能平静接纳一切的好与坏,能将自己变成一滴水融入海,去见识生活的种种可能。
此刻想想,虽走过不少地方,但最珍贵的记忆,并不是帝国大厦的夜景,伦敦丽兹酒店的下午茶,机场免税店不断上升的肾上腺素;而是台南农场阿嫲午后熬的冬瓜茶,西安小导游在车上收到假币后的哭泣,贵州深山里老乡煮的一锅公鸡粥,在皖南深山九曲十八弯后,九死一生偶遇的那片贡菊花田。
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渐渐意识到,人其实很像植物,不同水土会养育出完全不同形态不同脾性的植物。没有最好,只有不同。而旅行的意义,大约就是见识各种各样的不同,从而不再大惊小怪,慢慢长出人生的“钝感力”。
前几天小儿突然喟叹:“人生才几年,疫情已三年”。一惊,发现他在念电视上的广告语,哑然失笑。想想,又有点感伤。童年是最好奇的年纪,本应该在这样的年纪多走走看看,埋下种子,打下问号。可惜这三年,打下的是顿号,现在,该重新起笔,写下一个字了。
打起精神。没看过世界,谈什么世界观。2023,让我们继续出发。

去远方
◎米肖
疫情三年以来,深切感知到一双无形的翅膀被生生折断,对于外界的触感渐趋陌生,甚而麻木起来。壬寅年夏,北方一座海边小城连续盛邀两次,均因高中风险地区的划分而不能成行,殊为遗憾。整整一年,仅仅外出一次,循着陶潜的足迹,走了一趟江州,不曾预料过的乏善可陈。整个人仿佛一枚钉子被嵌入日子的木桩中而生了锈,内心世界暗哑无光,灵气不复再来。
终于等来自由行走的日子。杭州文友第一个发出邀请——纵然是友人间的客套,却也心旌摇曳一番。是啊,二三小时车程,早晨买张高铁票,还能赶得上吃一餐灵隐寺素斋,踏着落叶小径下山,沿西湖慢逛,走走停停,或许是日暮时分便到了满觉陇,随便坐在一株枯树下,饮一盏淡茶。倘若不急的话,就近下榻于西湖边小旅馆,翌日继续朝圣各方……每次去杭州,总嫌时间不够用,如若置身南宋,连临安小镇也要去访一访才好。
还想去苏州。距上一次,一晃十六年往矣。也不知那些古巷可在了,一直记得采芝斋的枣泥饼,甜度刚刚好。那个深秋,我坐在银杏树下晒了一中午的太阳,并将一块枣泥饼当了午餐,四周静谧无声,唯余落叶簌簌,秋意冉冉……那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有一个朋友去了云南。她在洱海边的步道骑自行车,一边是白云缭绕的苍山,一边是绿钻一样的洱海,鸥声如雨,碧波荡漾。通过她的镜头,大理上空的云永远那么飘逸,有着仙气的,一团一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我一路追着她的微博,神魂俱颠。她去了寂照庵、感通寺,高山玉兰正值盛开季,一树一树的洁白,让所有的形容词都失色。冬樱的绯红,凌霄的灼黄,九重葛的紫……瞬间点燃了我的生命力,我跟着她一路神游,去逛早市,那些熟悉的胡萝卜与内地都是不同的,是绯红色的,还有那些巨大的笋,新鲜的芭蕉芯子,碧绿的蔬菜:隔着几千公里,我也能闻嗅到云南特有的红泥气息,带着一点儿腥气的,接近于薄荷、紫苏的香气,当真沁人心脾。
这位朋友走的是小众路线,避开了大众景点。她一边走一边感悟:“保持对生活的热情,保持对万物有灵的信任。”
我的对于生活的热情,也只能在远方的异乡去建立——整个人重新涅槃,身心皆活,抛弃一切凡俗羁绊,每走一段旅程,皆重新活过一次——每一日的我,都是新我。不论精神层面多么困厄,但眼里一定有光,温暖自己,照亮世界……旅行可以将人的杂质祛除,摒弃俗世杂念,眼界顿时清明深邃,一如伫立繁星之地,宇宙如古画徐徐,我被嵌入时间的节点,目送斗转星移……整个人生变得可歌可泣而荡气回肠。
文学与行走,始终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成全,互构起昔年彼时当下未来。
一直有一个心愿,遍访古寺,写一部访寺书,或许需要十年时间、二十年时间。云台寺、雪窦寺、感恩寺等等这些古老的地方,我都不曾去过。这些小小心愿如一团团微火,被我紧紧拢于手心,深怕为过路的长风所熄灭,而格外的可珍可惜。
人类一生,极其短暂,终究比不过飞鸟行迹。北京的雨燕,每年都会有一次长途旅行,它们旅行的终点站在南极,时光流转,再自南极回到北半球。还有大雁、斑嘴雁们,它们的一生所迁徙的路途永远长于人类,它们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群体。去年深秋的一个凌晨,早早醒来的我,忽然听见大雁南迁的声音,如此真切,如此动人心魄,总是叫人无以言……北雁南飞的身影里,深藏着小小人类对于远方的向往,远方好比新生的代名词,未知的不曾抵达过的地方,星光一样不灭。
每年元旦,都会听一场现场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如一份星空下的迎新仪式,有着环球同此喜乐的在场感。2021年,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没有一名观众;2022年,稀稀落落坐了一千名观众;今年,大厅内座无虚席,当镜头扫过那些来自全球各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肤色的乐迷们,我的喉咙似乎被什么给堵住了,颇为哽咽……失去的日子,又重新回来了。

旅行的意义
◎小麦
踏进2023年的曙光,一切如新。
回想那些仅仅一个多月之前的事,恍如隔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居然是无比贴切的一句话。那些曾经的禁锢制约,随着国家的新政一下子消失了。2023年,是可以无限希冀的开始,如果说过去的一年只能埋首眼前,无法追问未来,那么2023年,就是是可以打开搜索,想象和安排飞行旅程了。
今年想去黔东南。祖国的西南,云贵川,好象也就贵州没去过。
2004年,在云南玩了半个月,以丽江为中心,去了泸沽湖,走了虎跳峡,还在密密雪花中造访了中甸香格里拉,参拜了松赞林寺。最为难忘的当属徒步虎跳峡,这是世界十大经典徒步路线,要花整整三天。隔着一条金沙江,我们走在哈巴雪山上,对面的玉龙雪山看着全无风采,雪都没什么,就是光秃秃的。高山峡谷,烈日大风,走在其间,是极其凛烈的实感。早晨出发的时候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到中午就脱得只剩下了短袖t恤了。第一天晚上住在峡顶,半夜大风呼呼,突然就把扣着的门吹开了,三个女生作伴还是吓得惊叫起来。第二天,我们就是穿越了峡谷,坐船渡过了金沙江,来到了大具。晚上大家终于洗了澡,吃罢夜饭,围坐在农家院子里,看着不远处的两座雪山,头顶着一轮明晃晃的月亮,啊,那一刻的澄澈与沉醉,真的是永远难忘。
至于四川去过的地方就太多了,成都重庆都专门去玩过,尤其是2005年国庆,跟朋友去了四姑娘山稻城亚丁后回来,特意在成都住了一周,周围都去玩了一圈,去都江堰看工程,去春熙路看美女。关键是每天吃火锅,当时的蛙蛙叫才三十八块一锅,就是牛娃火锅,另外就是每天吃柚子,至于冷锅串串,热锅串串更不在话下,那么狂吃狂玩一周吃下来,居然也没上火也没长痘痘,当地确实养人。
重庆不止是我徒步三峡那次,坐水翼飞船从奉节逆流而上,朝天门下船上岸,玩了几天。更有一次是因为朋友要去考察当地餐饮,然后我们结伴飞去那边吃喝玩乐了一周。说来搞笑,那次除了我们按既定安排去吃了一些特色的地方,考察了一些美食店,最大的收获居然是去了三次奥特莱斯,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回来,也算是每每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的地方了。
今年如果说国内有机会能走的话,先去下贵州,再去黔东南逛逛就是最好啦。夏天的贵州城是避暑胜地,那边的山山水水对我来说吸引力一般,但是好吃的一说起来就眼冒金光,所以,也许这是今年夏天最有可能实现的心愿之一了。
说到境外,好象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但去年被《我们的蓝调》《通往机场的路》这两部韩剧深深打动,从而觉得,济州岛的风景对我还有点吸引力。济州岛对我们是免签,完全可以说走就走,听起来也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一个所在。
我仅有的几次出国旅行,现在想来,居然还蛮好笑的,去了那么多国家,走来走去,居然到现在为止,也没走出亚洲。2004年的普吉岛。2009年的马来西亚,槟城,兰卡威。2010年的越南胡志民芽庄美奈。2012年的缅甸,仰光,蒲甘,茵莱。2017年的柬埔寨暹粒。
真的都历历在目,所有的回忆凝成时光的珍珠,证明生命不曾虚度。
旅行的意义究意是什么呢,如歌中所唱: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看过我埋葬记忆的土耳其……那些名字后面跟着的故事,想到就怦然心动的场景,可能才是我们真正旅行的意义。
2023年,愿你我有机会去飞。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