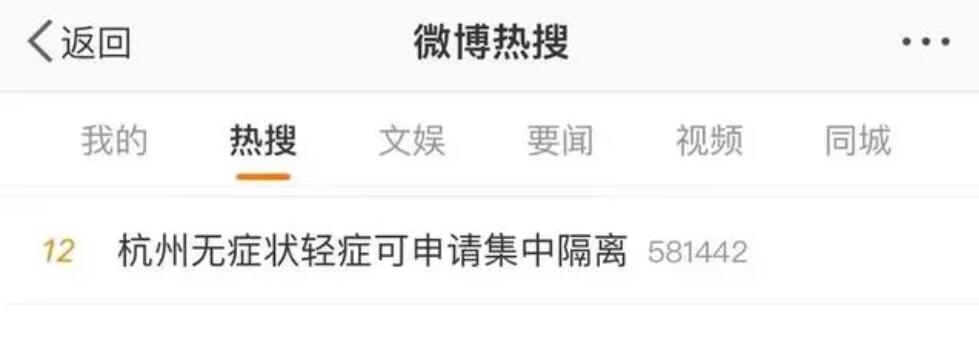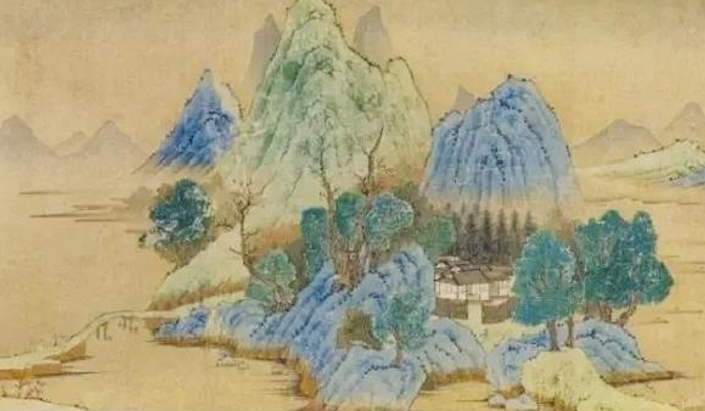年二十九那天终于闲下来,跑去省图借书,正好看到在举办《舌尖上的春节》新年主题展。全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新年,也都有各民族独特的“年菜”。一圈转下来,发现除各种肉食外,出现最多的是糯米制品——米粑、年糕、粽子、五彩糯米饭等。
年菜中,我最喜欢的一道糯米制品是炒米。糯米煮熟晾至半干,炒制金黄微糊。炒米不仅口感香脆,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健脾开胃,除烦止咳。日本有一种玄米茶,用炒米和绿茶拼配,也有消食暖胃的作用。
小时候过年,奶奶早早备好炒米,做各种炒米糖——有些放花生,有些揾芝麻。麦芽糖熬出一锅糖稀,将这些食材搅拌成一块,干透,用大白刀切成一块块,装进黑釉大肚坛,上面盖一张珍贵的塑料薄膜,再塞上一只巨大的棉布塞子。我自幼嗜甜,跟在奶奶屁股后面,从干炒米开始吃,一直吃到装坛,眼巴巴望着她,她总是一边叹气一边又掏出几个塞给我,“过年还要来人噢。”
今年过年什么也没采买,小零食全靠朋友们众筹。富平的柿饼、东北的的松子、糖村的牛轧、厦门的糕饼……都拎回家给老人了。唯独留了一纸袋肥东炒米糖,甜到齁,咬一口米渣乱飞,但里面有我奶奶的味道。
大年三十晚上喝鸡汤,特意舀了几勺炒米泡在汤里。这个吃法是大学同宿舍的王胖子教的。她是安庆姑娘,有个极能干的妈妈,每年寒假回来,总会带回一饼干桶的花生米和炒米,还有一锅蒸好切好的香肠。那时放学总饿,就会抢她的香肠泡炒米吃,再夹上一筷宣城的腌香菜,绝配!
二十多岁时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写某个飘雪的冬日,夜奔回阴冷的徽州老宅,给叱咤半生的大舅送葬。文中有句话印象深刻,“过了四十岁后才明白,人生不过迎来送往。”我也到了四十岁的年纪,能体会到这句话里的寒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人生的秋季,既有灿烂,也有哀伤,更多是要学会释然。
今年我家的年饭特别简单,一是因为之前“海啸”击倒一大片,老人不敢出门采买;更重要的是,这帮做年菜的生力军真忙不动了。
孩子奶奶祖籍上海,往年家里的年菜,有很多麻烦的菜式——糖醋熏鱼,五彩皮冻,红豆沙八宝饭,大肉元宵,没一道是可以一次成型的。往年爷爷会固执地卤一锅年卤——猪舌,猪肚,牛肉,鹌鹑蛋这些,今天也因为清洗不动而放弃。我说去阿明买点酱牛肉呗。爷爷摇摇手,说吃不下。我也明白,谁也不贪那口吃的,放不下的,大约是春节忙碌的厨房和热腾腾的锅气吧。
我二姑已71岁,进入腊月后,还是给她的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每人各腌了一刀肉、一只鸡、一只鸭、一条鱼、一张猪脸、一串鹅肫和两只猪耳朵皮,晒好,装袋,再一家家送来。这件事,她做了二三十年。我真不知道,一个佝偻身体的老人,在乡下冰凉的自来水里,是怎么坚持一件件清洗、腌制、晾晒这些咸货的。大约是父母早已不在,弟妹吃到这口熟悉的味道,才算有家吧。
年三十那天,二姑来我家吃午饭,总共六个人,我妈端了十几道菜出来,我都惊了,和十几年前在乡下过年时的菜式一样——咸鸡咸鸭咸鱼咸猪耳先来一套,然后才是新鲜的鸡鱼肉蛋再来一套,最后才能轮上两道清淡点的蔬菜。
年轻时,恨透了这样的年菜,每次都像瓜地里的猹,上蹿下跳,嚷嚷没吃的。我妈每次都慢悠悠地说,“你吃白菜呗”。现在淡定了,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内心秩序,这些秩序,是由过往的日子,一行行书写代码构成。这些代码里,有他们童年的饥饿,兄妹相依为命的冬夜,青年时的茫然,中年的意气风发……节俭是秩序,忍耐是秩序,亲情是秩序,咸货也是秩序。
尊重每个人内心的秩序。年味可以变,但不要淡,那是家的味道,更是希望的味道。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