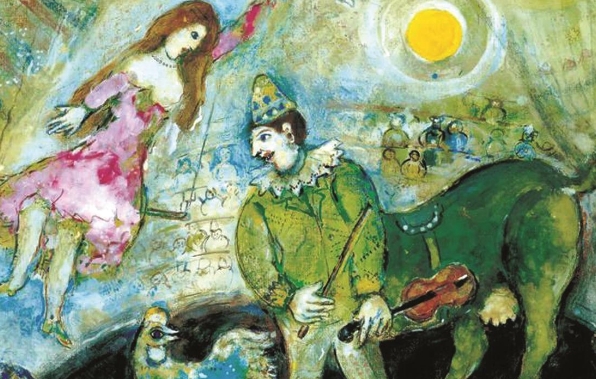东北的“冬”
◎杨静

第一次去东北,正是隆冬。20多年前的一个春节,南方“小土豆”把自己里三层外三层包裹起来,踏上了前往东北的旅途。
首站是长春,没有直达专列,需从蚌埠或北京中转。火车很慢,空间交错,骤然压缩,两天一夜都在车上,相邻铺位的旅客热烈闲谈,下车时,几乎处得像老朋友一样。
一路北上,满目浓绿渐成千里冰封。从零上8度的地方,来到零下28度的北境,下车那一刻,冷凉彻骨的空气将人包围,感觉不是“冷”,是“透”,寒气仿佛x光,瞬间把人从外到里照了个遍。好像夏天做凉面,将面条从热锅里捞出来,再放在凉水里一湃。对,就是“湃”,南方“小土豆”被东北的凛冽冰镇了。
所幸很快又上车,待到进入室内,抖落全身衣物,则又暖和得像夏天一样。朋友是长春土著,住在红旗街上,屋里地暖烧到最热,穿短袖,光脚,啃一块老冰棒或是糖葫芦,再啜一个冻梨,窗外雪花飘飘,只有“惬意”两个字可以形容。
猫冬生活,温暖而幸福。也出门玩,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到位,在运动中并不感觉太冷。坐54路有轨电车,去南湖公园,湖水冻透了,全部结成冰,在湖面上溜冰梯、滑爬犁,还有骑马、开小汽车之类的项目,大人孩子你追我赶中,都是热力发动机。
都说南方是“冻人不冻物”,北方则是“冻物不冻人”,经历了才真正体会到。初次的东北行还收获了“意外”礼物,之前大概从中学起手脚生冻疮。“一年冻,年年发”,每至冬季,满手冻疮苦不堪言,不能根治。那次东北的极寒之旅,带着一手冻疮去的,不知是因为被更寒冷的空气“湃”了的原因,还是被室内的温暖治愈,回到合肥,冻疮全部消失,再未复发过。
次年再去东北选择了国庆假期,打算看看“北方之秋”。真实感受,还是经历了一次“冬”。
那次跟着东北一个户外俱乐部去爬黑龙江的两座山。第一座是五花凤凰山,山腰下展现的正是浓烈的秋,枫叶红得鲜艳,落叶松金黄夺目,鱼鳞松、樟子松不动声色,仍是伟岸的绿。枫的鲜红,落叶松的金黄,樟子松的绿,加上高高的白桦,丰富色彩绘成巨幅画卷,美丽极了。
等爬到山顶,却遭遇了一场初雪,白桦林披着白雪,形面璀璨的树挂,阳光穿破乌云在远处的群山之巅横成玉带,阳光漫漫洒下,远山间的五花画卷隐约可见,身旁却是伸手可触的冰雪。秋冬交替,出现在同一空间,宛如梦境。
跟着又去登了黑龙江最高峰大秃顶子。那时的大秃顶子完全没有开发,原始森林状态。有靠谱的人带队,荒山野岭也不怕。正赶上一波冷空气降临,山下小雨,接着是雹子,爬到山腰雪花纷飞。把背包里所有能裹上身的衣物全部穿上,还是冷!
当晚在山顶扎营。一早,费力拉开帐篷门,厚厚的雪一下跌落。大雪是飞舞了一夜啊!天地白茫茫一片,上面是白云,下面则是白雪,整个连成一体,而我们,就如山上的一树一石一草,自然而然。
后面又坐了6345次普慢,就是现在俗称的“雪国列车”,历时24小时,穿越大兴安岭,去北极漠河。
才十月初,漠河已是零下10度,供上暖气了。假期尾声,没有什么游人,我们住在北极村里,沿着黑龙江边散步,江对岸,是俄罗斯村落,有俄罗斯人骑着摩托出门,不需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还去拜会了漠河乡政府。时任乡长侯振坤刚从俄罗斯考察回来,他滔滔不绝介绍漠河的方方面面,还把各样规划拿出来给我们看,说漠河未来要建滑雪场、飞机场,洛古河村要建黑龙江源文化碑,胭脂沟要建金矿遗址等等……如今,漠河早已成为南方“小土豆”们心心念念打卡的旅游胜地,那些项目应该早就建成了吧。
再想到东北的黑龙江冷水鱼、大骨头炖酸菜、汆白肉血肠、土豆炖大鹅、苞米团子、蘸酱菜……唉呀,口水流了一地,必须赶紧再安排一次东北行。
东北记
◎南窗纸冷

东北今年大热,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攻略、视频、新闻,是想装看不到都难的地步……东三省我是都去过了,只是心心念念没有坐过一次雪国列车。今年本想从哈尔滨坐个卧铺去漠河,但如今尔滨那么火,决计还是等一等,稍稍避一避热度,把机会让给还没去过北方的人。
说起来,哈尔滨给我的印象还是“好吃”。第一次去哈尔滨时还没到三十岁,南方人第一次去那么北的地方,走在路上,忽而就会飘起鹅毛大雪,那份心里的惊异,大约和如今的“南方小土豆”无异。大街上吃马迭尔雪糕,路边的商店卖着貂,走得累了,钻进一家店吃粉条炖大马哈鱼,太好吃了,十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吃过那么美味的鱼。马迭尔雪糕后来全国各地都有卖,但我坚持认为,当年吃的味道才是最对的。
秋林红肠也是当年首次吃到,直到如今,我还喜欢自东北买红肠。有时不想做饭,切切一碟子再炒个青菜,就能送下一碗米饭。米,也是东北大米,感恩黑土地的福泽。
小时候在北京上学时,河道结冰是常事。可到了哈尔滨,松花江结冰的盛景还是大为震撼了我。冰层很厚,隐隐透出江水的碧色,有着阡陌纵横的裂纹。我穿着雪地靴,穿过江面去了太阳岛,那天足足走了十三公里,竟一点也不觉得累。
后来陆续走完了东三省。因着去辽博看大展,接连去了好几次沈阳。我总是住在沈阳故宫边的一个快捷酒店,地段很好,只要一百多元一晚,还供早餐。曾有一次为着赶时间,只匆匆忙忙吃了半碗面,餐厅阿姨大着嗓门问我,姑娘,你再带上两鸡蛋,路上吃啊?
去吃老边饺子。自门外就能见到屋里的热气腾腾,我只有一个人,被领到楼梯下的一个小独座桌儿。我要了盘饺子,炒了盘蘑菇,上来之后才发现吃不完,真吃不完。分量太大,在我南方足可供两人食用。
辽博馆藏古书画是中国书画界的半壁江山。我在那里先后看了《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瑞鹤图》,后来还看了吉林博物馆借出的《文姬归汉图》,大概这也是生在这个时代的幸运之一,千百年来最好的东西,竟然能亲眼见到。
去长春时看伪满洲国皇宫博物馆,那日极寒,我穿上了全部衣服,还是被穿堂风吹得瑟瑟发抖。长春的游客不多,有着非常经典的东北城市风味,日光冷淡,天黑得很早。巨大的烟囱悬在城市上空,不分昼夜喷着白雾,吹远去,就成了云。路边未融化的积雪在朔风之下碎成了小小的冰粒,经过的车又将它们卷到了路面上。一阵风吹起,好似一层雾笼过。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很火,长春有冰雪新天地。一样有冰雕、烟花、娱雪项目。去长春时我带了孩子,我们两个拖着重重的雪圈,坐在上面,自冰雪坡道上滑下来。都是新手,我们两个伸着四条腿,向下扒拉自己的雪圈,呼的一声,下去了,一路冰花四溅,甚至会吃到嘴里。那份轻盈感后来曾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大约,也会滋养小孩的童年记忆吧?
寒风吹彻
◎钱红丽

一位旅行北欧的博主说:试过在冰天雪地中等车吗?那感觉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站牌显示还有8分钟,这是北欧第一次对你说谎,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一段文字感同身受,寒风中的8分钟,当真漫长如年。不曾体味过严寒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想得到吗?一段文字,令我在精神层面寒颤连连。想起那年寒冬在天津高铁站,不知为何,北方小姐姐那么急迫,竟然提前20分钟将寥落的几个乘客放进月台枯等。
北方的天空高远空阔,青杨树叶子落得一片不剩,全世界的萧瑟荒凉,齐齐聚集了来。伫立月台的我被寒风围困住,哀告无言,瑟瑟发抖……相邻的一对夫妇试图前来攀谈,我痛苦地挤出笑容以示回应,再无热量接话——怕一张口,冷风倒灌,从头到脚穿心凉。
那是一生中最漫长的20分钟。至今忆及,我全身骨头还是凉的。凉透了,一直暖不过来。
天津那座酒店作为旧时代的国宾馆,颇有些年头了,庄严灰旧,遍布光阴的质感,何谈双层玻璃?洗澡时热水器不工作,重新换房间,立刻感冒,翌日涕泪横流。午夜,朔风哨子一样尖叫,偶尔切换为呜咽之声,更多时像极防空警报,让我深感孤单、惊惧……那种孤立无援,也像小时迷了路,一直走不出那座山冈,眼看太阳落山,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的恐惧啊。
北方何以给我这样一个下马威?这些年,走过一些地方,偏多温暖之地。一桩桩一件件回忆起来,遍布琥珀一般的暖色调,俱成美好往事。但北方那种倨傲的冷,一点点逼出个体生命的不得已。四五年过去,依旧不能面对自己泥足于寒冷的软弱无能——真是对我灵魂的极大摧残,无力反戈一击。
那几年,忽遭工作环境的暴击,一口气尚存,总归要离开的。可是呢,临了又被理智劝住了,反复拉锯战般消耗自己,一如那个朔风呼啸的午夜。
假若三十岁就好了。到底未能挪步的原因,多是我残山剩水的身体再也不敌风寒。后来,每每遇事举棋不定,便想起天津高铁站那瑟瑟发抖的20分钟,漫长无告地望着列车来临的方向,冻木掉的两只脚,来回切换着轻轻跺在水泥地上,愈焦急,时间愈显漫长……
小时候的寒冬,也冷。坐在教室,双脚木然。但小孩子有热望,下课铃骤响,便得救了,风一样跑出教室,小伙伴们默契地依墙而立,相互挤暖,体内的血液快速流动,我们的脸庞彤红,手足俱暖。这珍贵的10分钟赋予童年深厚底蕴,一辈子忆及,都是甜的。童年是趋光的,勃发的生命力天生可以御寒。如今,我生命的烛焰渐委,纵然一息心力尚存,肉身的庐舍难抵风寒。
同是寒冬,我又去了石家庄。去酒店,一路均是灰苍苍的,天是灰的,整座城是灰的,默默跟了我们一路的太行山,贝叶经一样似压于箱底几千年的灰尘扑面,别无一点生机。天色向晚,众人站酒店前,等车间隙,忽地一阵妖风,眼前一棵小叶榆树,瞬间卸落一身黄叶,片甲不剩。眼前一幕,令我呆怔,大为惊骇,确切地说,是破防了。这北方的风,来如惊鸿,一如鬼拍掌,何等残酷,一掌下去,诸叶皆尽。
在我久居江淮的经验里,树叶是一片一片一天一点落掉的,宛如大提琴的沉思慢板,自深秋拉到初冬,一片一片由绿到黄,春花十万如梦里……众叶凋敝,至少要用去两周时光。
谁曾想,在北方,万物凋敝仅仅数秒?
坐在酒店随便一个角落,均能望见太行山剪影,不得不想起荆轲刺秦的遥远旧事。正是在这太行山脚下,燕太子丹易水河畔送荆轲,用文人的语言概括: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死别啊。也只有苦寒北地,可以产生这样的文学。倘若在温暖的杭州,唯有折柳作别了,或者《梁祝》缠绵悱恻的“十八相送”。越剧是何等的至柔至糯呢?杭州这样的南方之城,无论如何产生不了荆轲这样的壮士。
壮士注定要为苦寒所锻造。
诗人树才老师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人只有呆在寒冷的北方才能写出点东西来,要是整日流连于杭州,置身山光水色之中,哪有心思创作呢。
斜风细雨柳绿花红之地,最能消磨人的心性。高寒国家如俄罗斯,何以产生那么多杰出天才?无论文学界、音乐界、绘画界,一个个均是苦寒中来的,活出了个体的尊严。
所居酒店,设有河北省图分馆,借出几本好书。一夜夜,枕着风声批阅,不觉夜深——纵然窗外朔风呼啸,到底有书籍作伴,灵魂有所安顿,不再惊惧。
并非虚妄之言,文学确乎可以用来防身的——假若什么都失去了,不必害怕,至少还有文学这根定海神针呢。
之后,离开石家庄,去了正定,拜访隆兴寺,见了那尊翘着二郎腿的观世音。菩萨那么美,晦暗的寺里,伫立久之,默默许了一个愿。
今天凌晨,看见一个博主录了自己孩子的一个小视频。一岁多的孩子看见阳光洒在沙发上,高兴坏了,用小小的手去捉……底下几百条留言,一样讲到自家孩子种种天真之事。我津津有味读下去,真是一个美好早晨,纵然窗外中度雾霾的天气,也不必介意。
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向苦而生吗?我们要时刻像幼童那样,不失一颗赤子心,懂得每一缕阳光的珍贵,开心地向每一日致敬。虽然冷冽酷寒,还是向往北方,东北、内蒙、新疆,一直是梦寐之地,总有一天抵达。
那年寒冬的清晨,我自正定离开时,天降大雪,华北平原一夜白头,叫人始终不能忘记。
尔滨二三事
◎风举荷

吴伯凡有次做节目,说自己大学毕业时,有个同学考上美国研究生,回家向老父征询意见,老爷子沉吟半晌:“你去也行,我们就当你死了。”吴伯凡198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人的心中,美国确如天边一样遥远。
我爹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生,我问他,为什么当年会报考合肥工业大学?他漫不经心说,因为那是我爷爷靠步行一天一夜就能走到的学校。当年以他的高考分数,上清华也没什么问题,但农民的儿子一心想考“工业大学”,全国有两所工业名校——哈工大和合工大。
哈尔滨,明显我爷是走不过去,那就选合工大。多年后我第一次去哈尔滨,坚持要去哈工大看看,仿佛完成我爹的一个心愿。
哈工大挺神奇,校区被一条大马路割成两块,沿围墙走半天,也只能从侧门进入校区,漂亮的大门正对着车水马龙的马路,想拍个全影得站马路中间,罢了。傍晚,我在校园遛半天,抓了一哈工大学子问:“你们学校有没啥景点可参观?”那娃笑了半天,“我们学校只有宿舍和教学楼”。还是在哈工大食堂边发现一家小小文创店,哈工大的文创,全是卫星和导弹,牛不牛?!
哈工大一直不是教育部直属的高校,原来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现今隶属于国家工信部,是一所有军工和国防科技背景的高校,是公认的“国防七子之首”。打个比喻,哈工大于哈尔滨,有点像中科大于合肥,低调到陌生。
有几年,走南闯北,最喜欢坐两家航司航班,一家山东航空,另一家龙江航空。山航真的极少延误,经常延半小时,提前十分钟给你落地,让人怀疑机长们是不是组团去俄罗斯留过学。
喜欢龙江航空,是因为即使经济舱座位也极宽敞,大约为了配合东北大高个。据个人经验,龙江航空的空姐空少们,身材最挺拔,颜值最高,洋气。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重要的交通枢纽,自然成了商贸聚集地。加之清政府对东北开禁,中原人开始“闯关东”,哈尔滨人口不断增长,国际性商埠的近代城市雏形日益显现。
哈尔滨作为这条铁路线上的最大城市,吸引来更多外国人。先后有33个国家16万余侨民聚集这里,19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各种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哈尔滨曾是当时的北满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国际都市之一。
哈尔滨一直有“东方莫斯科”和“东方小巴黎”之称。只是在过去的30年,东北发展出现断崖式滑坡,作为七普期间全国唯一一个人口负增长的省会,哈尔滨常住人口从最高点的1100万,到2021年跌破千万大关,东北再无千万人口大城市。
今年冬天这波泼天的富贵,不是尔滨总算学会了切冻梨,而是全国人民重新发现尔滨之美。
2019年夏天,第一次去哈尔滨。那年索菲亚大教堂在检修,没能进去。夏天的傍晚,教堂广场上的喷泉很漂亮,还有一阵一阵的白鸽。正瞎转悠,看见一支西洋乐队,穿着正式演出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旁边站了一圈穿汗衫和大裤衩的当地百姓。看了旁边的介绍才知,每年夏天都有哈尔滨之夏的小型音乐会,在广场上不定期演出。
晚上去逛中央大街,满街都是墨绿色的马迭尔冰棒车,买一根,一路啃一路逛到防洪纪念塔,路上有很多给游客画碳素画、素描画的小摊,那些摊主的气质也非常艺术家,间或还有人坐在那里演奏小提琴,那一瞬,好像重回巴黎小丘广场。
哈尔滨真的是个特别美好的城市,有着老钱风的优雅。
前几天翻到一条短视频,那个做索菲亚大教堂蛋糕的姑娘,录视频时哭得稀里哗啦,“真的只有哈尔滨人才懂”,“也不是因为蛋糕生意变好了才哭,而是看到自己的城市变好了,真的很开心”。
我的眼眶也跟着红了,为她,为她的城市开心。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