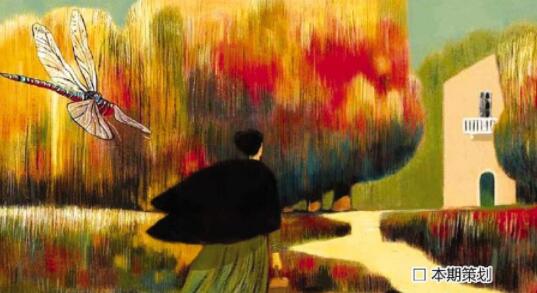夜半醒来,忽见枕畔一团银白,用手触摸时,却发现原来是一片月光。像一只闪闪发光的犁铧,明月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卧室耕成明暗两半。我索性将窗帘全部拉开,披衣起身,坐观明月。
这是东南方向的处暑之月,明月在空,只有半圆。半圆的月亮竟有如此强大的光芒,我对仰视的明月肃然起敬。天空是灰蓝色的底子,浮飘淡淡云絮。和白昼里的蓝天白云不同,底色黯淡,半月通明。七八颗星星像宝石散落,眨巴着睡眼,它们同样集中在东南方向。我想起去广西龙脊梯田时看过的一道风景,名曰:“七星伴月”,那是大地上的壮族民歌,而此时此景,是真正的天空之镜。一架飞机飞向明月,很快与月亮擦身而过,机上的人也在看月吗?那又是怎样一番天空之境呢?
“一帘风月王维画,四壁云山杜甫诗。”少年时,我将这副对联用楷书书写在老宅的大门上,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意象。不承想,三十年后,留宿故乡时,一帘明月这样真真切切前来探望我,像探访一位老友。月光如水如茶,予我款待,没有半点责备的意思。而我自觉惭愧,很久了,我将明月这个好友弄丢了。忙忙于尘世,碌碌于霓虹,我不曾将一颗心交给明月,接受月光的洗礼。
我的心也像月亮一样透明吗?带着疑问,推门出户。子夜的乡村如同一幅版画,黑白交汇。弯弯小路,像白豆腐;夹道野草描摹着暗影。竹林、柳树树冠是黑的,边际线则浮泛着云雾般的月光白。池塘里浸泡一轮明月,仿佛随时可以打捞。探身水际的青石板,如同黑色琴键,等候棒槌敲击。泥鳅于池藻弹跳,蛐蛐在草丛演奏。乡月朗朗的夜晚,是一曲弦乐绝唱。可惜,我五音不全,无法将这些美妙的音符如贝多芬那样记录下来。
遥想当年,东坡先生就是这样披衣出寺的吧?“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寥寥数语,他写得何其简洁。或许,这正是明月给予他的启示:文章只要通透就够了,何须繁文缛节?在子夜,游月归来的东坡先生是要点灯、研磨才能书写的,仿佛还在梦寐中,他撂下那几行肥硕大字,像胖胖的月亮,然后,酣然大睡。这样的夜游,何尝不是一首明月诗?
和先生不同,我记录下一帘明月,是在手机的备忘录里,是在千年之后。
(何愿斌)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