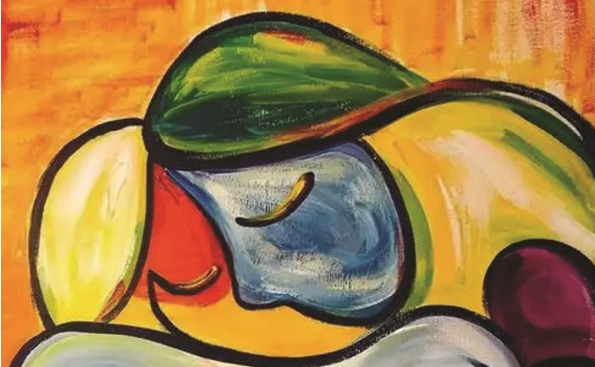人间处暑秋
□杨丽丽
处暑的风是带了秤的,称走了伏天最后一丝黏腻,秤杆一翘,漏下的全是清清爽爽的凉。晨起一件外套,袖口扫过桌面时,带起一阵风,有了清冽的意思。
案头的茉莉开得正好,却也透着点见好就收的懂事。花瓣不再是伏天里那种水润润的白,多了层雾状的粉,像敷了层薄纱。香气也淡了,若有若无地绕着鼻尖,不像大暑时那样霸道,非要钻进人心里不可。
街上的人换了衣裳。姑娘们的裙摆长了些,料子也厚了,走起路来沙沙响,像秋草在风里低语。街角的桂树,枝丫间藏着小小花苞,像撒了把碎米,凑近了闻,已有淡香,不似茉莉那般躲躲藏藏,倒带着点笃定。
去公园散步,两个老人打太极。招式慢悠悠的,抬手、落掌,都带着股从容不迫的劲儿,倒比盛夏时那些跳广场舞的热闹,更合了这节气的脾性。银杏叶还绿着,却比往日硬挺了些,边缘泛着浅黄,像被谁用金粉描了边。长椅上落了片叶子,拾起来看,脉络清晰得像老人手上的青筋,藏着一整个夏天的故事。
湖边的芦苇开始抽白,毛茸茸的穗子在风里晃。水比夏天浅了半尺,能看见水底的卵石,附在上面的青苔也瘦了,不像伏天那样绿得发腻。我往水里扔了块土疙瘩,惊起两只蜻蜓,一只是红的,一只是黄的,飞得都比夏天慢了,翅膀扇动的声音也沉,像驮着什么东西。
沿着湖岸往前走,撞见几个孩子蹲在石阶上,手里捏着网兜,正盯着水面上的浮萍。往日里疯跑着追蝴蝶的劲头收了些,说话都放轻了声,怕惊了水里游得慢悠悠的鱼。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攥着片梧桐叶,她忽然抬头问:“奶奶,叶子是不是在攒力气,等天冷了就变红呀?”
风从湖面卷过来,带着点水腥气,却不黏人了。岸边的垂柳把绿裙子收短了些,枝条不再像盛夏时那样沉甸甸地垂到水里,倒像梳过的头发,轻轻巧巧地晃。有老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摇着蒲扇,却不怎么扇了,就那么有一下没一下地晃着,扇面上的荷花图案褪了色,倒和这秋意里的清淡合了拍。
菜市里倒热闹,只是少了些聒噪。卖秋茄的摊前,茄子紫得发暗,带着层薄薄的白霜,像蒙了层雾。摊主是个穿了件长袖蓝布衫的胖婶,笑着招呼客人:“这茄子再不吃就老了,秋后的菜,一天一个模样。”旁边鼓鼓的毛豆堆得冒了尖,剥开一个,豆粒圆滚滚的,带着股清甜味,不像夏天的豆子,总带着点生涩。
路边野菊开了零星几朵,黄灿灿的,藏在草丛里,不像春天的花那样招摇,倒像攒了一整个夏天的劲儿,就等着这阵凉风吹过,慢慢把颜色铺开。有只麻雀落在电线上,歪着头梳羽毛,梳着梳着,忽然扑棱棱飞走了,翅膀带起的风,吹得旁边的狗尾巴草晃了晃,穗子上的绒毛,沾了点阳光的金。
想起昨夜的月亮,比夏夜的清瘦些,挂在天上,像谁晾在竹竿上的银镰,把最后一点暑气割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的仙人掌,尖上冒出点新绿,硬挺挺的,倒比夏天时精神。原来秋不是一下子来的,是风一点点称走了热,是叶一片片攒起了黄,是日子在晨露和夕阳里,慢慢换了件清清爽爽的衣裳。
吃新豆
□米丽宏
八月,豆田青郁郁。豆棵半人高,父亲进田看豆荚长势,一俯身,背影就融在了绿里,斗笠像一个金黄的圆漂浮着。
这块黄豆地,第一次来看是“五一”假期,那时星星点点的“丫”字,着鹅黄淡绿的童衫,横成行竖成列,像小学生做广播体操。第二次来是端午,豆苗儿已哗然齐膝,叶子毛茸茸攒满地垄,绿水漫灌不见地皮。豆花也开得扑棱有声:粉白的,花朵上沾着粉粒子,一摸腻手;白里透紫的,素雅而神秘。白的紫的搭伙儿开,像繁星降落碧海,闪闪烁烁,摇摇曳曳,让人心喜。
如今再来,已是万棵挂荚,一簇簇豆荚团在豆棵胯部,拥挤着,熙攘着。青青豆荚,珠胎暗结,像怀孕的豆妈。荚皮被豆粒撑得鼓胀胀,一颗一颗,硬挺饱满,好像憋着一股劲儿;剥开豆荚,豆粒青青的色泽,润润的手感。拿到鼻子底下一嗅,一缕清鲜的豆腥气,清甜纯净;放口里品品,淡淡的草甜,轻轻的豆腥,如此时刚刚起步的秋风,轻盈,细嫩,又软又萌。
处暑,正是吃鲜豆的季节。父亲让我们采一篮子,回家蒸豆。放点盐,锅里一压,软软糯糯,香香甜甜,那是毛豆吗?那是节令的嫩汁、八月的时鲜呀。
毛豆这东西,不仅不挑地,还肥地。植株上那些根瘤,就像一个个造肥场。再瘠薄的地,种一季黄豆,好了,往下种啥长啥,黄豆替你养地了。
村子里,红白喜事和年节的豆腐,乃至豆油、豆浆、豆汁、豆皮、豆酱、豆芽、豆腐脑,哪个缺得了黄豆哇?看眼下这黄豆的长势,收获也不过一个月的光景。等它们再蓄蓄粉,收收水,叶也卷了,荚也干了,籽也硬了,秸秆儿木质化了,隔荚皮可看出豆粒儿的肥瘦了,好,那时节我们再来帮父亲割黄豆。
我们再去杨树湾的绿豆地摘一篮绿豆。地只有一分,每年产下的豆子,足以供应我们姐弟三家一年食用……等豆罐见底儿,新一季绿豆又荚黑粒儿满了。
绿豆的绿,很迷人,亮,纯,明艳,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那种幽邃的绿。有一种牡丹叫“豆绿”,那是华美贵族对民间之美的追慕。牡丹和绿豆,绿得真像,也都美。
橱柜里有一个灰蓝色土制的瓦盆,常用它生豆芽。清水泡胖绿豆,看它努出尖尖嘴儿,就挪到能吸水也能沥水的瓦盆。湿布覆盖,一天淋一次水。三五天,豆芽暄蓬蓬拱出了盆沿儿。抓一把豆芽和着红辣子爆炒,或者过水拌凉菜,那天然的豆香、脆脆的口感,每每吃得欲罢不能。
有句俗话:豆芽到老一根菜。是说它混得人缘和光景都够呛?我还挺喜欢这种喧嚣中的冷静独立呢。绿豆,芽嫩绿,叶翠绿,花儿黄绿,籽粒呢,幽绿。绿豆做糕做汤,是或深或浅的绿。这种叫“绿”的豆子,真是把“绿”铺排到了生命的每一个细节。
眼前的地里,绿豆长得随性,植株下部结着荚,有的荚黑了,有的还绿着;植株上部开着花,花儿明明黄黄的。这样的情形总是让人踌躇,割呢,它还有荚在生长;不割呢,有的豆子已长成,一性急,就会荚皮爆裂,豆子像微型导弹一样发射到远处。
这是处暑的美好,新秋的馈赠,我们总会充满新奇地去接受时令的美意,一年一度,从不缺席。
把夏与秋缝在一起
□白丽霞
丝瓜藤在晾衣绳上打了个结,把最后一朵嫩黄的花垂在晾着的蓝布衫前。母亲正翻晒竹匾里的芝麻粒,她抬手抹汗时,腕上银镯子碰响竹匾,惊飞了檐下啄食的麻雀,这便是处暑了。
处暑的晨露总比往日重些,沾在豆角藤上,像谁撒了把碎钻。邻家李婶挎着竹篮摘秋葵,裤脚扫过草叶,带起一串晶莹的水珠,落在青砖地上洇出浅痕。“这天说凉就凉了。”她对着蹲在篱笆边看蚂蚁搬家的我笑,“前儿个还热得直扇扇子,今早就得套件薄褂子。”我伸手捡起一片梧桐叶,叶脉上还挂着露水,凑到鼻尖一闻,竟有股清甜的草木气。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堂屋,在八仙桌上投下窗棂的影子。奶奶坐在竹椅上剥莲子,竹篮里堆着青褐色的莲蓬,剥开时露出乳白的莲子,莲心是嫩黄的。“吃些莲心败败火。”她把剥好的莲子塞进我的嘴里,自己却把莲心都收进小瓷瓶,“留着泡茶,秋燥的时候喝正好。”
村口的老槐树下聚着些纳凉的老人,手里摇着蒲扇,扇面上印着“春耕夏耘”的字样。李叔叔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响,说:“今早去田里看稻子,稻穗已经沉甸甸地弯了腰,再有个把月就能割了。”王婶手里择着豇豆,豇豆是紫皮的,择下来放进竹筐,紫莹莹的一串,像谁串起的玛瑙。远处的稻田里,稻草人戴着草帽,衣角被风吹得猎猎响,惊走了偷食的麻雀,却惊不醒趴在稻草人脚下打盹的老黄狗。
傍晚的霞光格外柔和,把天边的云染成淡粉。孩童们在晒谷场上追逐,踢起的谷粒在空中划出金黄的弧线,落在草垛上,惊起几只蚂蚱。母亲站在灶台前烙饼,面团在案板上“咚咚”响,鏊子上的饼鼓起金黄的泡,香气混着院里桂花的甜香飘出老远。父亲扛着锄头从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土,进门就喊渴,母亲递过一碗晾好的绿豆汤,绿豆汤里漂着颗蜜枣,喝下去,从喉咙凉到心里。
月亮升起来时,蛙鸣已经稀了。院墙边的蟋蟀开始唱歌,声音清脆,像谁在弹拨琴弦。奶奶搬张竹床放在院里,铺上晒干的稻草,躺上去沙沙作响。窗外的老枣树上,最后几颗红枣在月光下闪着红光,像遗落在枝头的红玛瑙。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接着又归于寂静,只有蟋蟀的歌声在夜色里流淌,伴着渐起的秋意,漫过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这便是处暑了,像奶奶纳鞋底时穿过的线,不紧不慢地把夏与秋缝在了一起。热还在,却添了几分收敛;凉已来,又带着几分温柔,就像灶台上温着的米酒,余温里藏着醉人的甜。
草虫吟
□刘建峰
处暑的日头是收了性子的。先前总把柏油路晒得冒白烟,如今斜斜地照在院墙上,倒像掺了水的蜜,稠是稠,却少了灼人的烈。门楼下的竹床被祖父搬进堂屋,说“过了处暑,夜凉浸骨头,潮气伤身体”。
风也换了脾气,不再卷着热浪扑人脸,摸上去是温吞的,像祖母刚晾好的米汤。到了黄昏,这风忽然就停歇了,连墙根那丛牛筋草都支棱着叶片,一动不动,似乎在等什么。
蝉鸣早几日就稀少了。先前整树整树的“知了——知了——”,吵得人午觉都睡不安稳,如今只剩零星几只,嗓子也哑了,“知——了——”拖得老长,尾音里带着点颤抖,像漏了风的风箱。它们是熬不过处暑的,祖父说,“伏天的虫,火里生。处暑的虫,土里藏”,话刚落音,最后一声蝉鸣便断在暮色里,世界猛地安静下来。
这静,是给虫儿们腾的场子。
头一声从柴草垛里钻出来,细溜溜的,“吱——”,像谁用针尖挑破了秋夜的薄纸。停顿片刻,西墙角的砖缝里应了一声,更沉些,带着点沙砾感,像石碾子碾过干硬的土块。跟着,菜畦边的豆角架下、葡萄藤的老根旁、堆着南瓜的草筐底,数不清的嗓子一起亮了,蟋蟀的“瞿瞿”,蝈蝈的“聒聒”,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小虫,发出“咝咝”的微响,缠成一团,把这处暑的夜填得满满当当。
祖母搬个小马扎坐在院里,手里攥着补了补丁的蒲扇,却不摇,就那么支着下巴聆听。月光爬上篱笆墙时,她鬓角的白发泛出银辉的光芒,跟草叶上刚凝的露水似的。“你听东头那只,”她忽然扯我的袖子,“调子发飘,定是昨夜让露水打了。”我屏住气,果然有只蟋蟀的声儿忽高忽低,像踩在摇晃的草秆上,随时要跌落下来。
葡萄藤下藏着另一种不知名的虫子。声音细细的,像纺车转得飞快,“吱吱——”地绕着垂下来的青葡萄转。葡萄粒刚有指甲盖大,被月光照得透亮。这虫儿不掺和别处的热闹,总在藤叶最密的地方哼唱,像个守着秘密的老妇人,数着粒儿过日子,一粒,两粒,数得专心又虔诚。
露水漫过脚踝时,虫鸣浸了水汽,声腔也变了。先前的脆生劲儿淡了,添了层湿漉漉的黏,听着像隔着层浸了水的棉纸。蟋蟀的声儿沉下去,像掉在井里,嗡嗡地发闷。那纺车似的细响却亮起来,带着点清凌凌的凉,顺着藤架爬上来,沾在胳膊上,激得人打了个轻颤。远处的稻田里,偶有蛙鸣滚过来,被露水打湿了翅膀,落到院墙上时,只剩半截模糊的尾音,像谁在梦里含糊的呓语。
祖母起身回屋时,我跟着她往屋里走,看见月光把她的影子铺在地上,又被门槛拦腰截断,像幅没画完的水墨画。
灶上温着的南瓜粥该好了。揭锅盖时,白汽“腾”地涌出来,混着南瓜的甜香漫到院里,虫鸣忽然就低了半拍,像是被这热乎气烫了嗓子。祖母盛出两碗,撒上点桂花糖,瓷碗相碰的脆响里,虫声又慢慢涨起来,裹着粥香,裹着月光,裹着墙根砖缝里藏不住的秋凉。
后半夜被尿意催醒,听见窗外的虫鸣稀了些,却更加清亮了,像被露水淘洗过。摸黑穿鞋时,踩在地板上的响动惊得院角一只蟋蟀戛然收声,等我重新躺下,它才试探着“瞿”了一声,跟着,远处又有两三只应和起来,零零落落。
天快亮时,起风了,带着明显的凉意,处暑的清晨,也裹着虫儿们未唱完的调子,慢慢亮起来,和着远处稻田里最后的虫吟,把这秋的序幕,拉得又长又绵。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