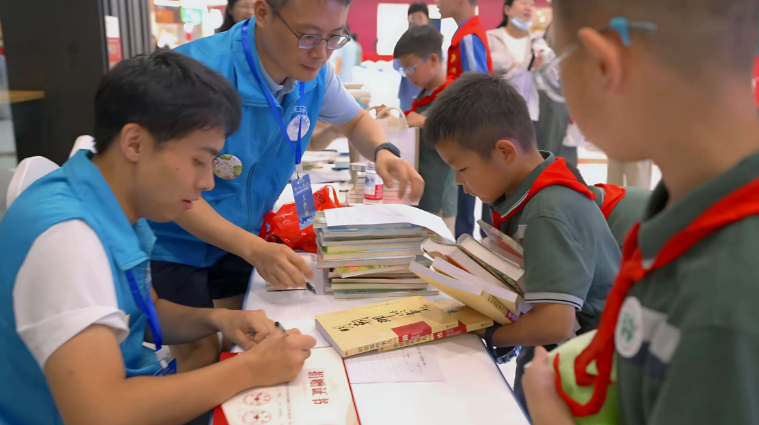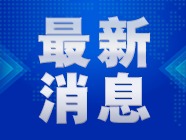小时候贴的膘发挥了作用
□ 花菜
小时候我是个瘦小孩。我妈和我姥姥经常提起,我出生的时候瘦得像个小猫,手像鸡爪子那么小。一直到上小学,邻居还会常打趣我:“家里好吃的是不是都被你爸妈吃了?”
80后的童年,大多家里没那么宽裕,但吃饱饭是没问题的。但我小时候不爱吃饭,追着小孩喂饭这样时髦的事,我妈几十年前就干过,为了劝我吃饭,给我的稀饭都是加了糖的。我爷爷是个乡村医生,他跟我妈说,你这样不对,饿她两顿就吃了。我妈就很生气,怎么能让孩子饿着呢。后来我自己有了小孩,想跟她说,我爷爷说得对,想想终究没敢说。
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我每天还有一份鲜牛奶喝。我妈每天把牛奶煮开,里面再打一个鸡蛋。但是我也不领情,一吃鸡蛋就头晕,一喝牛奶就肚子疼,真是难伺候。
因为一直是个小瘦子,每年暑假回老家,姥姥总要想法子给我贴贴膘。她带我赶集,买“青鱼”回来炖汤,然后看着我吃。青鱼就是甲鱼,一大碗甲鱼汤连汤带肉吃下去,再挑食的小孩都服服帖帖的。后来,每次在婚宴上吃浓油赤酱的“霸王别姬”,我都想起甲鱼汤,不用这么复杂,炖汤最好吃了。
暑假里还是抓“知了猴”的好时节。知了在地下蛰伏十多年,破土而出时就是逮住它的最好时机。天刚擦黑,姥姥就带我去抓知了,拿着大手电筒。田埂边的大杨树林子里影影绰绰几团手电筒的灯光,那都是拎着蛇皮袋抓知了的老乡。姥姥并不擅长这个,我们忙活一晚上一只也没抓到,只捡到几只蝉蜕。回家路上,遇到拎着蛇皮袋满载而归的熟人,送了我们一些,总算没白跑。“极致的美味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姥姥起油锅,知了下锅炸熟,连盐都不用放,焦香酥脆,真是难以形容的好吃。
平日里,姥姥如果进城来看我,总要买肉和鸡蛋送来。我小时候最喜欢吃肉烧茄子,姥姥每次来都买五花肉给我做。北方的茄子圆滚滚的,或紫皮或青皮,偶尔还有白皮。五花肉先下锅,加水炖过一会后,放切成大块的茄子,炖到肉和茄子俱软烂就出锅了。吃的时候还要舀一小勺菜汤拌在米饭里,真是满嘴油汪汪。
可能是小时候贴的膘真的发挥了作用,我渐渐从一个小瘦子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少女,然后成了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从上大学离家,从没有为“胃口”发过愁。大三的时候考研,跟隔壁寝室一个姑娘每天相约上自习。但我俩最有劲头的是晚自习前那顿饭,二里街、官亭路都吃遍了,最常吃的是沙县小吃,一人一笼蒸饺,配上一盅茶树菇老鸭汤,偶尔还要加一份炸馄饨。上自习时,还要揣上两包安庆老奶奶花生米,我说你知道吗,花生米配橘子特别好吃。她说我小时候配黄瓜吃,黄瓜心掏出来把花生米塞进去,特别好吃……吃货的世界里,我们惺惺相惜。
胃口好的人对食物特别宽容,南甜北咸都能吃出滋味来。刚毕业时,在苏州工作,那里的盒饭炒青菜都要放糖,同屋的是个东北姑娘,三天两头吃泡面。我觉得青菜是甜了点,红烧肉甜甜的还蛮好吃的。
但我妈至今坚定地忽略我已经成为一个胖子的事实。在家吃饭,但凡我先放下筷子,她总要满脸忧虑地问我一句:“就吃这么点?”只好端起碗再吃一点。热爱吃饭,总归也不是坏事。
不贴都是一身膘
□汪漪
虽还是酷热难耐,不少人开始忙着贴秋膘了。处暑之后,各类果实成熟,胃口好转,一批健脾温补的食物也上市了。
以前没有空调,夏季胃口不好,一个暑假总要瘦几斤。每年秋季开学前,爷爷都会给我们称下体重量个身高。爷爷拿直尺压在头顶上,尺端顶住门框,铅笔在此处画下横线。门框上,从下往上,一年又一年的刻上身高。称体重可就是个大工程了。一家人齐上阵,用绳子系住被单两端,小孩坐在被单上,绳子挂到秤杆上。一手拎不起来,爸爸叔叔用扁担抬起来,爷爷移动秤砣,记下数字。即使正是长身高的年纪,“苦夏”之后都会轻几斤。
没事,秋天到了,胃口打开了。秋梨上市,芡实成熟,鲫鱼丰美。汪曾祺也说过,芡实老了,夏天也就过去了。
芡实也叫鸡头米。因其果实为球形,顶端有宿存的鸡喙状花萼,形如鸡头而得名。秋季鸡头米成熟,没有大人出手,小孩很难吃得上。果实藏在叶片下,翻开叶片,割下果实,茎秆果壳上全是硬刺。戴上手套,用剪刀把壳撬开,翻出果球,鸡头米藏在白色的花房里,像剥石榴一样,一个个抠下来。抠下来的鸡头米,就是种子,外面还有一层硬壳。一层又一层的,剥掉这一层壳,才能吃得上。正是如此,鸡头米的价格一直不便宜。
收割回来后,小孩拿上果球,一般不会独享。喊上小伙伴,你一粒,我一粒,细细地用牙嗑开硬壳,吃下果仁。果仁硬实,淀粉含量高。勾芡的芡,此前就是芡实的芡。
对于小孩子来说,鸡头米不甜不咸,口感并无优势,但它长得圆圆白白的,像一颗颗小珍珠,粉白可人,且来之不易,所以珍惜。
鸡头米采摘繁杂、颜值高,且健脾祛湿、滋养补肾,药食同源,颇受文人喜爱。曹雪芹就很喜欢鸡头米,《红楼梦》中多次现身。宝玉曾遣袭人送给史湘云的两样鲜食,一是红菱,一是鸡头米。他还创作了一道流传至今的名菜“大蚌炖珍珠”,即鲫鱼炖芡实。雪白滚圆的芡实塞进鱼腹,恰如蚌含珍珠。《随园食单》里也有芡实的很多做法,磨碎做成糕点、芡实蒸老鸭等等。
在老家,除了作为鲜食小吃,芡实一直都是一道素菜。最常见的就是用来煮粥、炖汤,也可单独蒸煮。妈妈把它放在陶罐里,在火上慢煨,火候到了,一股清香,撒点糖,粉粉糯糯的,口感厚实又清爽,很奇妙。
小舅妈在杭州,经常寄晒干的鸡头米来。小舅妈寄东西都是整箱整箱的,两大包鸡头米,妈妈用来煮粥、炖银耳,从秋吃到冬。
饮食习惯也与区域有关,牛羊肉在我们老家不是荤腥主流。我家基本不吃牛羊肉,不吃鸭鹅,妈妈有时炖了鸡汤鸭汤,需要摊派任务,强制喝。但鱼虾和米饭一样,得天天有。
鲫鱼在秋季与春季最肥美。这时节,鲫鱼烧毛豆,鲜香扑鼻。多年围观我也学会了,且拿手。大火将锅烧红,倒油,撒盐,放鱼,不要急着翻面。待鱼尾焦黄,加醋、老抽、姜片,加水。水烧开后,放毛豆。毛豆的量不能多,太多会盖了鱼的鲜。
还有比鲫鱼烧毛豆更鲜的,那就是杂鱼烧毛豆。鲫鱼、白条、汪丫、草鱼,不拘什么鱼,手掌长,加一点河虾,仔细煎一下,倒入毛豆,香气四溢。用这个鱼汤拌米饭,不用菜,也能吃一碗。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哪还要贴秋膘,不贴都是一身膘,国家都在喊减肥。以前称体重,觉得特好玩,根本不关心数字。现在无比关心数字,也简便,站上电子秤就行,但是不敢啊,天天假装秤坏了。

秋补
□小麦
处暑过后,秋老虎一点也不逊色,太阳还是晒得皮肤生疼。但是,毕竟节气到了,出伏了,秋天第一件事就是要补秋膘,算是季节转换所需要的仪式感。
扪心而问,补秋膘这事,我不配。它应属于那些在夏天被虐过的人。有个朋友,体质孱弱,一入盛夏就苦不堪言,空调不止不能拯救,反而说开了空调全身酸痛,不开又如在火上炙烤,不动而全身出汗,如此受罪地过一个夏天,她往往要瘦好几斤,补秋膘简直是当务之急。但像我这般皮实的人,从不理解这般苦楚。我是随遇而安型,只要有空调,就能拯救一切。我的夏天从来是轻松度过,从无苦夏可言。
但毕竟是秋天了,我也煞有介事,发个微博,说你们补秋膘吗?配一个老乡鸡餐盘,喝点鸡汤吃个鸡汤面就算补了,但是,今年我想趁着季节的名义,做点有意义的事。
2025年的秋天,是我进入社会的第三十年。遥望当年,1995年的秋天,如黄舒骏歌里所说,张爱玲在秋天过了她最后一夜……那个秋风初起的季节,我从一个青涩学生成了社会人,有了第一份工作。时光荏苒,忽尔就是几十年,我已从一个县酒厂的化验员到合肥一个流浪者,再到今天落户喜欢的城市,成为一个新合肥人。在这从异乡变成故乡的沉浮里,我认识形形色色的朋友,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
他们的名字,或在纸质通讯录中,或在手机电话本里,更多的是,沉睡在彼此的微信聊天栏。他们一般不发朋友圈,我的世界寂静得像从未有过他们的痕迹,偶尔他们在我的朋友圈或是公号下留言,我才恍然,他们还在默默关注着我。
想起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拨通电话,真的能听出惊喜,我说,咱们太久没见了哦,但认识超过三十年了。大家不由唏嘘一下,立刻约好一个见面,一起补个秋膘,给岁月和我们的友情再次来个锚点。
见面,深深拥抱,笑着说彼此没变。但她真的变化挺大的,以前那个美丽温柔的女生,现在憔悴苍老好多,她说起这么多年都经历了什么,工作,生病,不得已辞职在家,孩子上学,陪读,老公职业上的危机。我默默听着,告诉她,她见过的那个前夫,不久我们就分开了。后来,我去这里那里,现在还在合肥,后来,我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是完全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告诉她,经常想起我们最初认识的时候,尤其是上次去省立医院,解放电影院地铁口一出来,我就立刻想起她,往事复活,她稳稳在中间。
是她带我吃了第一顿肯德基,在青云楼。是她给我买解放电影院对面那家好吃的粽子,解放电影院门口的油炸的鸡蛋吐司,也是她第一次带我吃。当时小心翼翼捧着那个纸包,觉得又甜又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她带我看电影,《碟中碟1》,汤姆·克努斯是那么帅。她带我去她家,红星路一号的省委大院,很旧,却很温馨,收音机频率停留在cri。她爸爸是社科院专家,到处是研究资料。家里的书一直排到屋顶,有一架梯子专门供上下。
她所拥有的,就是我憧憬中的完美生活。那个时候,我只有羡慕。有人天生就有母性,我觉得她就是,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在她面前,我事事处处像是被照顾的小孩。
如今,我请她吃饭,给她买好吃的,带她去有趣的咖啡馆尝新。我意识到,我们的位置翻转了,现在我可以照顾她了。不知这是应该欣慰,还是伤感。我对她说,以后有好的电影,我就去找她看,小孩都上大学了,她不该像以前那样不出家门。
感觉见了这个朋友,就如同给我的生活补了一个秋膘,补偿了岁月的亏欠,也让我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了更多盼头。甚至,生出念头,想去找更多的朋友,久未联系的。请他们吃饭,感谢他们的照顾。让他们觉得,当年的付出给了我多么大的影响,虽然,当时大家浑然不觉。
是人生的秋天了,但,秋天也挺美好的。
打牙祭
□张言
一个月前,菜园被我打理得乖巧有序,再回来,差点被泼辣的藤蔓绊倒。
末夏时分,纤细柔弱的丝瓜秧强悍无比,爬上纱窗,匍匐四处,比壮实带刺的南瓜秧还懂得攻城略地,墙角地缝被卷须勾连成片,因它才形成高低错落的荒园景观。
八十六岁的云奶奶瞥见荒园,拿起镰刀要帮我割草。不能再让八十多岁的人垦荒,再说,我也舍不得铲掉这片如荒地的菜园。野草丛生间长出的青菜蔬果,恰是我“贴秋膘”的牙祭。
“贴秋膘”充满吃的怂恿与正义,让人们吃得光明正大,毫无心理负担。
五六个老丝瓜悬在门头,进出有些碍事,可也没舍得摘掉。想等它们老透,内里变空长出瓜络,摘下煮水喝。丝瓜络煮出的水,黏稠润滑,入口清新,与石斛煮的水口感相近,同样能润燥,但在价格与取材上,对普通人十分友好。
嫩丝瓜遍地都是,随便扒拉几下藤蔓就摘了一堆。刮掉外皮,雪白瓤子比黄瓜还水嫩,轻弹一下便能碎成几截。香油爆香葱花,投入丝瓜,快炒几下,两个土鸡蛋淋入热锅。鸡蛋液立刻包裹住出过水的丝瓜片,蛋香含着瓜香,带领丝瓜一起在锅内翻滚,定型成块。不待起锅,倒进开水,汤汁瞬间腾起热气,刚擀好的新麦面条迎着滚浪下入,麦面的谷物馨香融入丝瓜鸡蛋的浓郁,一锅面条还未盛出,早已唾液翻涌。
吃罢回家的第一碗面,已有力气打理菜园。
红黄黑三色小番茄,在绿植底色里分外显眼。月余无人问津的生长,挂满果实的植株不堪重负,倒伏在草丛中。野生小番茄酸甜可口滋味正,一粒一粒仔细采摘,连枝头晒成番茄干的也一并采下,不可多得的自然产物,分外珍惜。采摘了半篮,鲜番茄洗净生食,番茄干装袋密封。
几个小孩见我在草丛中找来找去甚是有趣,也好奇地跟着翻找,他们踢开杂草丛,又找出十几个小番茄,攥在手里,欢呼雀跃着跑开了。
当初舍不得砍伐的野苋菜长得比玉米秆子都高,每个枝杈都结籽穗,成了麻雀食堂。我走过去,惊扰到茎秆上、草丛里觅食的麻雀,它们飞起,扑棱棱一群一片,热闹又喜庆,看得人高兴。
连砍了十几棵比我都高的野苋菜,才发现并想起野苋菜树下还长着九棵不同种类的辣椒,二荆条、螺丝椒、薄皮椒、彩椒……
彩椒被野草欺到腐烂,其他辣椒个个细长瘦弱,不敢支棱着长开。可到底还是扛住了,拌上面糊做成面辣椒,依旧辣得燎嘴。
刚炒好的面辣椒,滋滋冒着炸物酥香,夹在热馍热烧饼里,撑得鼓油油,双掌用力压按几下,使两者贴服合二为一,就是喷香的北中原菜夹馍。
田地里,玉米皮已经泛白,麦后玉米该收了。馋嘴小孩早早掰下几棒玉米晒干,小手一行行剥掉玉米籽,四处打听爆玉米花的老头儿有没有出摊。


 设为首页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